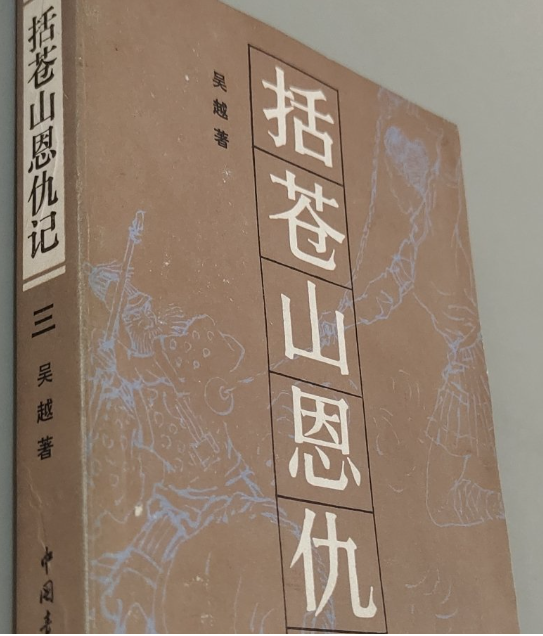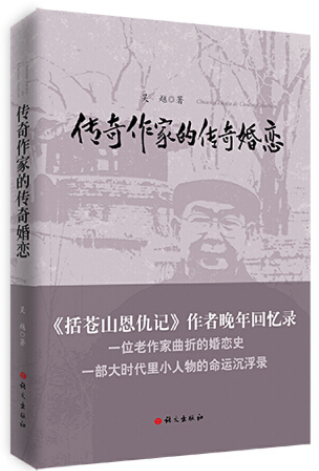| 老頭子吳越先生 馮知明 |
| 送交者: 石頭巷子 2025年11月09日08:08:5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1.吳越先生駕鶴西去一周年記
認識吳越先生是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情,迄今已經有40餘年了。那個時候,我在一家大型文學雜誌搞發行,它的發行量高達287萬,由分布在全國有八個大印刷廠印製。發行人員要在全國各地跑。我覺得每到一地,只了解發行工作,有點浪費精力和時間,便找編輯,可代他們拜訪一些沿途城市的作者,也讓雜誌社的差旅費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樣便認識了吳越先生。 2024年11月9日吳越先生駕鶴西去,享年九十有三,我半年後才從侯小強先生得知,他的形象一直縈繞於心,在法蘭克福這半月余,一直處在回憶狀態,已成就近萬言文字,以紀念這位亦師亦友的尊長。 那時,吳越先生住在北京府右街惜薪胡同一個小小的四合院,單位給他分的房子並不大,只是一室一廳一個小間廚房,家裡堆滿了書籍,顯得過於擁擠。府右街地處首都的心臟地帶,順着走到幾百米,便到了世界著名的廣場,騎着他的“二八大槓”幾分鐘即到。 那時他的小女兒吳永還是背着雙肩包上學的小學生,吳越先生在自家小廳靠窗處搭了一間只能撂一張小床的單間,供女兒居住或做作業。我到了之後,他說:“我雖知道你的旅差費是單位報銷,同樣也沒必要費錢。”便力勸我住在他家裡,讓女兒睡沙發,我住在這個小房間裡,一來二去,我便習慣住在他家中。吳越先生和他夫人樓阿姨在中國戲劇出版工作,中午在單位食堂進餐,晚飯時會等我一起吃飯。有時我來京,不巧他家裡來了客人,占了那個小間,他便騎着“二八大槓”帶我在胡同口轉兩個彎,入住由北京地下防空洞改成的簡易旅館:“只是晚上過夜住下,什麼東西都不要帶。”當年,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北京,都是這樣住過來的。 我與他是真正意義上的忘年交,我們之間相差足足有30歲年齡,而且一直不曾中斷過。我一直稱他為“老頭子”,同樣是幾十年沒有變過。有次他對夫人解釋說:“老頭子,是武漢人對老爸的稱呼。”他很欣慰我這樣叫他。他有些出版事宜委託我,也常會給我寫信,從來都是用“您”這個敬稱,可見吳越先生的謙虛。我印象中的老頭子,中等身材,不瘦也不胖,長年光頭,我想人老到一定年紀了,就定了型,從我認識他50多歲起到九十大壽,身體和面容看不出什麼變化。80歲迎來他的第四次婚姻,夫人是湖北宜昌人,新婚夫人小他20歲,新婚不久隨夫人回娘家,路過武漢時,我們請他,調侃這是“老女婿上門”,他對這種說法很受用,滿臉欣欣然的樣子。 記得他有個習慣,每天不管中午或晚上睡覺,無吸煙嗜好的他,要躺在床上抽半支煙,用他自己的話說:“把我熏暈。”一年四季戴着一頂軟帽睡覺;這個習慣已經被我傳承了,因為頸椎的毛病,大腦供血不足,戴帽子睡覺,保持體內溫度,使人睡得安穩。 他除小說家這個身份外,應是語言文字專家,曾師從周有光先生。他在2022年6月12日推薦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給我留言中,這樣寫道:“周有光先生,是我的恩師,是我的語言學啟蒙老師。1953年,我在上海,就認識他了。當時他剛從美國回來,在上海財經學院當經濟學教授。我1954年調北京,他比我晚一年,到文改會後出任第一研究室(漢字拼音化研究室)主任。我們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比如說:他奉命給上級領導起草有關文字改革的報告,就點名叫我去給他當助手。1980年,我住在文改會招待所等待分配,就經常到他家裡去。那時候他和倪海曙老師共同創辦《語文現代化》雜誌,周有光老師就和我合作:由他出主意,我來寫,把一個‘拼音文字實驗園地’完全包給我。雖然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署名,其實都是我一個人寫的。目的,除了實驗之外,也因為我住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沒有工資,連吃飯都困難,所以幫我‘找飯錢’呢!——這篇文章,是周有光口述,由別人記錄的。所以文字風格,不像是周有光的。但是很值得一看。” 他同樣是最早使用電腦的作家,那時叫“換筆”,他曾為中國作協開過“換筆”班,有一批著名作家皆被他帶入電腦,比如原中國作協主席韶華先生,著名作家張抗抗先生。我在同齡人中是最早使用電腦之人,同樣也受了他的影響。我是湖北普通話,發音不標準,他常笑話我:“吳越的‘越’講不清楚;把茄子講成了‘瘸子’。”因為發音有問題,漢語拼音學得不好,他便建議我用一個華裔法國人創建的拼形碼,這個碼現在很少有人會用了。它的詞庫很少,我曾輸入過許多成語以豐富詞庫,到現在我依然是用這個拼形碼寫作。它常讓電腦辨識成有毒軟件被誤刪。WindowsXP被淘汰時,我差點用不成了,通過他找到法國華裔的溫州親戚,正好這人的外孫家居武漢,告知我升級版和怎麼安裝。 吳越先生是個樂觀開朗的人,特別有耐心,我很少見他生過氣,整天樂呵呵的樣子。記得有一年,我隨他去單位,他與同事產生了一些糾紛,估計是別人講他“圖表現,攬活干,假積極,”他只是辯解“我浪費了幾十年的時光,現在只好夜以繼日把時間趕回來,願意多做點事,並非圖表現。”單位里各種心態的人都有,有人干有人看有人混有人心裡不平衡,這是常態,一個經歷如此坎坷之人,對人生已經通透,“圖表現”這種話,虧得那同事想得到說得出口。我還記得一次他送我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先生的精裝十六開本的《中國古代服飾史》,這本書至今依然在我的書架上。
2.苦難歲月的零星記憶
關於他早年的經歷,多是他與我幾十年的交流時,所獲得的信息,產生的一些記憶。2024年曾送我長達4卷本的自傳電子版,倒是詳細記述了他的一生。我之所以願意用存在謬誤的記憶來講述他的人生過往,是因為這樣視角獨特,他的形象更生動鮮活。當然不排除我在半年後得知他逝世的消息,腦海里一幕幕地再現與他交往過程有關的畫面。 吳越先生出身在浙江縉雲一個殷實的家庭,少年顯示出了他的寫作才華,青年時代便投身革命,通過他結識在武漢的侄子吳文兄,這是一個黑臉漢子,長久在火車機組裡工作,人很豪爽,他曾告知說:“我那叔叔,年青時追求革命,帶人去抄自己家,搞過‘打土豪分浮財’之事。”我曾寫過一篇介紹他的文章,記述了這件事,輕易不生氣的他,說自己侄子完全是一派胡言,並親自把這種表述刪掉了。我見他如此動怒,倒有幾分相信他年輕時的作為。便說:“老頭子,如果沒有這事,犯不着這麼生氣吧。”他聽了作聲不得。他們那個時代,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或受巴金先生《家》《春》《秋》的影響,以澎湃為例,帶人抄自己地主家,來散財分給窮人,這是一些革命者自述中常見之事,本人曾編輯過國共兩黨許多將帥體裁的傳記文學,這類事跡並不在少數。 後來,吳越先生寫過一部關於破譯密碼之王池步洲先生的著作,告知此人是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最早的人,由當時抗戰領導人蔣介石先生通報羅斯福總統,只是這位美國總統不以為然。通過這件事,他曾告知我,他隨部隊打到重慶,在蔣介石先生的地下掩體,通過蔣用過的電話講話,“聲音非常清晰,沒有一點雜音。”從他這些表述,可知早年參軍,還有他影集中戴軍帽登記照,也說明這點。復員轉業到了地方,如前所述,他曾與周有光先生一同從事過語言文字的研究,他曾幾次對我說,“壽命要活到像我的恩師那樣。 正值風華正茂的青春時代,便開啟了他命運多舛、屢受挫折的歲月,那時政府願意傾聽民間的聲音,鼓勵“大鳴大放”,吳越先生表現積極,被“引蛇出洞”了。還有一種說法,也是先生親口陳述,單位有“劃撥”指標,因為他為人開朗,又比較好通融,便把這個“人頭”算到了他的頭上。他下放時,“連辦公室抽屜的鑰匙也沒有交,領導親口說,過上三五個月或半年,單位便會接他回來的。”哪知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這些經歷,皆是他閒談之中零星地提及。首先說他的“吃”,有次不知怎麼談到了“幸福”這個問題,他的幸福觀,真是別具一格:“要說幸福,就是照得見人影的米湯糊糊加拇指大小的一丁點兒醬蘿蔔頭。”在長達二十幾年生涯之中,他一直處在三分飽七分飢的生存狀態中。我與他交往後的生活,他曾這樣表述,與他過去相比,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有“天壤之別”。 再說先生的病,有一年,他生了病,被查出肺部有一元硬幣大小的潰爛孔洞,醫生斷定少則三月多則半年,就會“閻王不接自己去了”。面對這個嚴酷的現實,他很快冷靜下來,想想自己在人間走了一遭,還是應該要留下點什麼。在羈絆期間,他便開始構思《括蒼山恩仇記》,那時不可能有成形的紙張供他寫作,往往從田間地頭撿些煙盒包裝紙,或小學生的作業本以及一些能書寫的紙張上寫作。面對一場絕症,他認為這是自己最有價值的事情,便加快投入寫作。就這樣忘記了病痛,半年後再去醫院複查,醫生驚訝於他的身體修復功能強大,那潰爛處已經結了痂,不藥而愈。 在相同時代背景下,同齡人的經歷雖有不同,但慘痛記憶是相似的,他講過自己同寢室一位老人的故事,聽後令人震驚。他說,那是個“大好人”,同樣慘遭厄運,這是一位事事為他人着想的人。他早就計劃自絕於人世,將自己最後一點錢作了周密的安排——買了一根麻線一頭拴在自己腿上,一頭拴在自己樹上,這樣大冬天他投水自盡時,人家不用下河去撈,只需把麻繩一帶,便把屍身拉起來了。安葬自己準備幾條麻袋,連挖坑的鐵鍬和鎬頭也準備齊配,更細緻的是留下了幫他收屍人酒錢和菜錢的酬勞,待身後諸事安排妥當,他才從容投河而去。
3.老頭子的四段婚戀
我翻看過吳越先生相冊,老頭子曾經是個英俊的年輕人,因為時代浪潮的裹挾,把他打入最底層,先是被錯劃,再就是被羈押,後來環境相對寬鬆一點,同樣是掉進沒有盡頭勞改農場的深淵之中。 在他80歲大壽時,我應邀參加他的第四次婚禮。吳越先生那天穿着一身新郎的中國紅的裝束,這個80老新郎,如此興師動眾,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給自己60新娘一個體面的婚禮,更是對自己的人生一種補償。 我參加完他的婚禮後,有感而發,就我了解他的經歷,寫了一篇《吳越和他的三次婚姻》,發給老頭子看,一起發了一通感慨,他再親自為我修訂補遺,加了不少的篇幅。老頭子意猶未盡,寫成了一本他三次婚姻30萬字的大書,更是他人生經歷的自述。 她第一次婚姻,記憶中女方是福建人,有一位女兒,起名“永”。他被羈押之時,組織上勸其夫人,要與他劃清界限,與當年許多錯劃成分的人一樣,不得已離了婚。多年後,他加了一個群,把他的大女兒介紹給朋友們,這個叫大永的女子,我們在群上了解她六旬有餘的年齡了,她是位佛教徒,在群里曾發布佛法要理。老頭子在2025年6月24日給我留言,告知大女婿不幸去世:“下午好!我已經睡醒了。大女婿意外死亡整一周。大永做了超度道場,舉辦了素齋紀念會。重新開始正常的單身漢生活。好在她習慣於他個人行動,對生活影響不是很大。” 2024年8月7日17:30再次給我留言:“以為我病得不輕。真的,我是病得不輕。今天早晨,高壓219!血管一破裂,我就玩兒完了!現在我決定後天(9號)去上海,跟大女兒一起生活一段時間,然後就打算上路了。”我勸他不要去:“建議老頭子不要動,北京稍涼快,上海太熱了。現在行走消耗精力過大,不好。”他對自己的身體越來越擔心,我一直勸他“對自己的身體要有信心。” 他回復我:“你不知道:大女婿意外地走在我的前面了!6月初,他們到南京去旅遊。回上海,到了南京車站,大女婿一看離開車還有一個多小時,叫我大女兒在車站看行李,他到附近公園去轉轉。這一去,就成了永訣!快開車了,打電話去沒人接。立刻報警,四處搜索,找到了屍體。估計是從山坡上滾下來傷了腦袋。終年不到七十。所以,我去上海,實際上是去陪陪她。無法改變了。後天就動身了。隨遇而安吧!”這是他第一次婚姻,讓我了解到的後續情況。 在勞改農場時,他儘管依然戴着“帽子”,組織上認定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分子”,環境相對寬鬆,成就了他第二次婚姻。對方是農場附近農村的女子,婚後,生育一女,依然起名“永”。那時真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狀況,用他的話說:“生了女兒,兩個大人都無法養活孩子。最後商量,讓女方轉嫁附近一位老中醫,這樣至少救活女兒的命。”我印象深刻,當時他陳述這些時,深深嘆口氣,滿臉哀色,面容沉重。後來,我在北京來看他,見到一個清秀可人的女孩,在北京高科技公司工作,叫他“姥爺”。老頭子讓她叫我:“舅舅。”把我稱讚了一通,我判斷這是第二段婚姻第三代的孩子。 第三段婚姻,是平反之後的事了。他曾簡單談及過,那時老頭子的老母親尚在,打聽到故鄉糧站工作的樓阿姨,是個大齡女子,由老母撮合,與他成婚。婚後一同來到北京,與他同在一個單位,記得她發揮自己的長處,做出納工作。我與樓阿姨接觸比較多,她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家裡常有朋友過來,她都能熱情相迎,對我更是親近一些。有次她向我抱怨,學校開家長會,老師說小永的作文有待提高,這是客氣話,講得不好聽,就是寫作跟不上。而老頭子是作家,作家的女兒作文寫不好,豈不是叫人笑話嗎?“你說對嗎?”她講話總喜歡以反問的方式結束。原新浪副總裁侯小強先生,曾來老頭子家做客,對樓阿姨印象頗佳。樓阿姨身患絕症,先他而去。有次我和他談及老人再婚緣由,他說,未必與情感有多大關係。老頭一向被老伴照顧得不錯,老伴先走一步,老頭的吃喝拉撒都成了問題,必須找個伴兒——“老伴老伴,老來作伴。”我記得他這樣解釋。 老頭子80歲第四段婚姻,與60歲宜昌女士成婚,據他講述,是在爬山時認識的。相信是他的熱情開朗感染了對方。婚後不久,他又去爬了香山,正好我電話給他,老頭子興奮地描述自己爬山一天,一點也不累,我恭維說:“老頭子不死,會長命百歲。”我喜歡聽他講話,他中氣十足,並不失幽默,聲音具有穿透力。 這場婚禮在一個小酒店裡舉行,參加婚禮的多是他親朋好友,不乏當今社會名流,這是我參加的最老人家的一場婚禮。這老頭子一副新郎做派,同樣也是一次飽經風霜之後豁達與開懷的見證,他當場即興表演了節目,記得唱腔類似一曲評彈調。我想他的第一次婚禮,那時革命者講究移風易俗,革命化的意味很濃,儀式感卻不足;第二次在勞改農場結婚,根本不可能有條件舉辦婚禮;而第三次剛剛平反之時,百廢待興,只是在老家請了兩桌酒席,雙方親友一聚只能算是作個見證。這次80婚禮之所以如此讓他開心,更是對他人生一次補償。正好邀請前往時,一位在德籍華裔科學家許國昌先生在京,聽說這是一位文化名家的婚禮,他有興趣隨我來參加,特意奉上一個紅包,以示祝賀,他見了難得一見的文化名人。事後,他感慨:“酒店檔次偏低,可見文化人的生存狀態並未提高多少。”他當然不知道,對於老頭子來說,是難得一次精心地籌備和安排。 我這些年來,參加過許多年輕人的婚禮,是一種習慣使然。而參加八十老翁的婚禮,便想到,有些事未必有年齡的區分,只要自己去做,永遠不會晚,這是這個老新郎的狀態給我的思考。回武漢後,我便撰寫老頭子前三次婚姻的文章。 看得出來,婚後的生活之於他,是安逸和溫馨的。除了那次路過武漢的“老新郎上門”外,還有一次,便是爬香山,他告知我“一點也不累”,表現出了婚後意氣風發的狀態。這一陣子,我們之間聯繫自然少了許多。 在2024年4月16日突然給我留言,告知他離婚了。我聽了大吃一驚,他80歲進入第4段婚姻,到了90歲時離婚,這段婚姻維持十年。 我同樣驚訝地發現,九十老翁也能陷入失戀的痛苦狀態。婚姻之初,老頭子曾告知我,他把北京市地段最優的房子賣掉,換成兩套,一套給女兒小永,一套留給他倆住,還說,要給她們倆各配一輛車。這樣的安排不僅有點經濟頭腦,對於建立兩人世界更是合理的。慢慢地對方似乎感到自己就像個免費的保姆,我想到網上流行的一件事,一位教授妻子故去,感到為他服務的保姆有情有義,便有意接納她為妻。保姆聽後,明確拒絕,她算了一筆賬,她每月包吃包住,除了節假日有紅包外,每月還有一筆7000元的固定收入,保姆一旦轉換身份成為妻子,她雖然換來了名分,這些待遇就會隨即取消的,因為哪有丈夫給妻子發工資的。 老頭子2024年4月24日再次留言,除了訴說他的痛苦外,同樣讓我了解他的複雜心態:“我現在也在後悔……我的思想還停留在50年代,所以出現了‘不適應’的矛盾。現在已經不可挽回了。” 從下邊的一段話里,可以窺見他的內心痛苦和遭受的打擊:“知明老弟:我沒想到我的健康受到不是一點點刺激,竟會‘急轉彎’到這種程度:現在已經渾身乏力,步履蹣跚,行動困難到連走到樓下院子裡都很難,更何況出大門了。加上一天到晚總是噁心要吐,什麼也吃不下去。雖然天天吃藥,可是血糖怎麼也降不下來。原來希望再活兩年,現在看來,能夠支撐到5月4日,讓我做完九十大壽,就算很不錯了。還有許多事情沒做完,不得不半途而廢。仔細想想,大概多數人和我一樣,雖然老人老了,還是雄心勃勃,可是歲月不饒人。生老病死,客觀規律。秦始皇、當代那位領袖,手握別人的生死,都想自己長生不老,可是,他們做到了嗎?” 有句話說,只有失去了,才知道應該珍惜,我力勸他去挽回。認為我自己可以做點工作,我與這位夫人有對話基礎,他們畢竟是生活了10年的夫妻,是有感情的,我來溝通,不帶觀點和偏見,也許可以起到一點作用。老頭子認為已經“無法挽回了”“反正離告別人世也不遠了。就得過且過吧。” 從老頭子這裡,我了解到了老年人的情感生活,在我看來,人老了,什麼都經歷過了,應該是心如止水,從他這裡,才知道老年的情感波瀾,顯得更加豐富和深厚。
4.2000萬字的作品,那是一座讓人仰止的大山
吳越先生是一個惜時如金,非常勤奮的人。我只要來北京,他皆要求我住在他家裡,後來換了新房子,我同樣在他家裡住過一晚。他每天都是凌晨5點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幾十年來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規律。不僅這樣,他具備與時俱進的能力,那時電腦和網絡剛剛興起,他編寫教材,有時還親自授課,我記得他編寫過50多種教材。甚至,這個不會把時間浪費到打麻將上的人,同樣編寫過一本教人打麻將的書,估計這是出版社的“命題作文”。 我對他的創作比較了解,加上做出版發行工作建立的一些書商人脈關係,給他聯繫過一些出版事宜。最早的一個中篇(或者是從他長篇節選),發布在新疆吐魯番的一個地級刊物上。記得南京一位書商,策劃了一個選題《泰國十日談》,他不足一個月便交了稿子。他創作狀況發揮較佳時,每日能完成一萬多字。 有一段時間,明清小說流行,老頭子劍走偏鋒,將用滬語方言寫成的小說,改成普通話,認為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剔除糟粕,保留精華,再就是普通話是當代通用語言,便於傳播。出版商認為如果用原書名,不利用於銷售,遂改名《花國春秋》《江南浪子》,因為是書商包銷,一次性給他支付稿費,至今我也疑惑這種嘗試出版方式,市場的接納度到底有多大。 在他一生寫作的2000萬字作品,後期主要是評註本,影響最大的還是他早年百萬字的鴻篇巨製《括蒼山恩仇記》,他曾告訴我,一次在北京新華書店簽名售書時,等簽售的讀者從三樓排到了一樓還拐了彎,這同樣也是人生的高光時刻。多年以後,出版社印製一批收藏的精裝版,他簽名親自郵寄,連續幾年皆有熱衷收藏的讀者郵購。 我常想到他那幾千萬言的寫作,這就是我人生的高山仰止。他早年熱衷於創作小說,同樣認為是寫作中成就較高的藝術形式。除了《括蒼山恩仇記》外,還有一部以勞動教養為背景180萬字的鴻篇巨製《悲歡世界》,這裡有許多親身經歷,當年在系統內評價甚高,並計劃重點推出。後推薦給領導審讀,哪知領導讀完後,給了四個字:“不宜出版”。他不止一次,希望我找下途徑,完成他的心願。 因為創作小說難以出版,使他頗受打擊,特別是第四次婚姻時,他被激發了很大的熱情,對傳統小說和經典名著進行現代版的評註,2024年2月4日他給我留言:“九點多了。我剛剛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初稿整理完畢。從明天開始到3月初,還有一個多月時間,我要儘快完成二稿,然後把《吳越文影合集》送到電腦公司去刻錄U盤。這個任務完成,我就可以鬆一口氣了。” 老頭子還有一個令人稱頌的好習慣,他會5年或10年,將自己寫作的文本,集中刻錄下來,難得他對我的這份信任,便會給我一個備份。到了2024年時,光盤已經容納不了,便改成U盤存儲。2024年7月5日,再次給我留言:“這是我今天下午剛剛完成的一本評註叢書。收到以後,請把它拷貝到吳越文影合集2024年版U盤中,地址是中華傳統小說評註本第一輯,就配套了。這一來,U盤就滿了。最好是把整個U盤複製到電腦硬盤中。”我寫得不多,至今只有500多萬字,用他的方法,集中整理了。 老頭子是個熱情開朗的人,他因為對網絡和電腦運用能力,結識許多AT行業的年輕人,幻劍書盟的創始人就是他介紹我認識的,原新浪副總裁後又出任盛大文學CEO侯小強先生也是由他介紹認識的,我們一直沒有中斷聯繫。記得我主持武俠雜誌工作時,展開過一個“武俠文學是否代表民族文學的大討論”,得到了空前的響應,引來一場持續數月的論戰,意見一反一正兩個方面,以老頭子為代表的,是否定我們這種提法的。新浪在推介吳越先生《水滸》評註版時,他邀請我參加,進而也在新浪平台上進行了論戰。當時陪我一同前往的還有幻劍書盟的站長死風先生,他事後評價說:“吳老中氣十足,發揮得最好。” 當年他住在惜薪胡同時,與之比鄰而居是劉紹棠先生也同時是他引薦的,我曾多次拜訪他,他有個小小四合院,每次把我送到院門口,當然他也說,就是國家領導人來我也是這樣的。劉紹棠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一直以大運河為體裁寫作,我還記得他說:“你們怎麼說,我也只能寫大運河,一直寫下去,寫到死。”他習慣用沾水筆寫作,每個字的豎畫,像往地下打了一個樁似的強勁有力。 在2023年5月10日他終於完成了自己的自傳,並直接將文本發給許多至親好友,他這樣寫道:“終於迎來了我的91周歲生日!我一生坎坷,多次接近死亡線邊緣,終因‘人生旅途’的任務沒有完成,一次次驀然回首。這個任務,就是吐我的絲,做我的繭。 “今天,雖然我肚子裡的絲似乎還沒有吐完,但是人生的道路,卻似乎已經接近盡頭。 為了避免像老友邵燕祥那樣:‘昨夜睡去,沒有醒來,也沒有留下遺囑’(他女兒給我的信),我這一年來,就集中精力,在完善我寫了十幾年的回憶錄。現在終於寫完了,居然四大厚本,將近1700頁。自己看看,也就那些破事兒,沒有幾件是有價值的。 “在今天這樣的時代,我想說點真話。因此,儘管都是我個人一生所經歷過的或者看見過的聽到過的芥末小事兒,反正也沒有什麼隱私可言,倒不妨拿出來,公之於眾,和那些跟我一樣茶餘飯後有空閒時間的親友們分享,也算是一個耄耋老翁在 九十一歲‘華誕’中送給諸位的一份兒生日禮物吧!……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親友們,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晚年吧!” 他第4段婚姻終結後,從他言談和字裡行間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種緊迫感,還有身體每況愈下,定期會把他的身體情況通告給我,有時也會發布到他的朋友群上。2024年5月22日給我的留言,表達了他即將歸去的坦然心態:“早安!早上五點醒來,一直眯到六點半才起來。昨天拉稀,還好,只拉了一次。可是今天兩條腿,像麵條一樣軟,眼睛也模模糊糊的,看什麼都不清楚。我知道,這是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自然現象,沒有什麼可奇怪的。順其自然就是了。我這個人比較達觀:活着干,死了算。橫向比較,我比許多人強多了。54年前,那麼多人死在勞改農場,我卻掙扎着活下來了。這後54年,不都是白撿的嗎?所以要滿足。一滿足,就心寬。該幹什麼還幹什麼!等到哪天您再也收不到我的報平安信,就可能永遠不能再見了。是不是?老朋友!”他的幸福感和滿足感,便是來自那幾十年羈押歲月。 我與老頭子互發短信和視頻,持續在2024年11月2日,於11月28日,看了一篇寫池步洲的文章,轉發給他,以及前邊發的幾次,他皆沒有回覆。他發起的朋友群,同樣也靜悄悄的。令我有些擔憂起來,如果他真的仙逝,至少在他群里的大女兒,會向他的朋友們通報一聲。他定期會告知身體狀況,我恰恰在這一段沒有收到。我有些預感,忙到群里搜尋他的大女兒,不知是退群或是不確定哪一位是大永,只能作罷。群里的人多是他的老友,如果有什麼消息,大家會通報一聲,令人奇怪的是,看來沒人知曉他的情況。 我想他作為文化名人,如果仙逝,應該媒體上有報道。查詢“吳越”同名同姓者不少,沒有他任何消息,或者我用的360搜尋功能並不強大。到了2025年上半年,侯小強先生告知我,吳越先生已經逝世,並發來浙江麗水市網媒的報道(他搜尋到的),老頭子已於2025年11月9日逝世。這兩年侯小強先生定期會和我提及他,問候他的身體狀況,我們不免感嘆半天。老頭子是個很生動的人,至今筆耕不輟,還在完成出版社的約稿,他的離去,竟然如此安靜,不知是他勞碌一生,想靜靜地離去,還是家人有意為之,並不願發布訃告。 這半年,得知他去世之後,我腦海里時時浮現起這位睿智者音容笑貌,我與他有四十多年的交往,我想把許多深刻的記憶,一幕幕地講述出來,以紀念這位耄耋老人奮鬥的一生。
吳越,原名吳佩珏,1932年5月出生,浙江省縉雲縣人。十七歲參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師從周有光、倪海曙先生從事語文研究。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勞改二十多年,歷盡磨難,性格不改;年已耄耋,仍筆耕不輟。其一生愛好讀書、寫書,共寫有文學作品57本2000多萬字。對當代文學有三大貢獻:一是“文革”期間在勞改農場的田邊地角偷偷兒寫成一部以官逼民反為主題,結合描寫縉雲縣民俗、人物、山水、風光的超長篇歷史文化小說《括蒼山恩仇記》,三卷五冊200萬字,198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暢銷70萬套;二是出版了《水滸傳(少年版)》《吳越評水滸》《吳越品水滸》等系列專著,共100多萬字;三是與戴春合作的史詩式長篇小說《悲歡世界》三部曲,180萬字,以描寫1957年—2007年五十年間的勞動教養生活、新疆流放生活,得到了中國法學會法制文學研究會屆法制文學原創大獎賽的長篇小說獎和表彰。晚年從事明清小說的評註和語文規範化工作,小有成就。此外出版有電腦教材55本,近1000萬字;純學術著作《浙江省縉雲縣方言志》一冊。
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 法蘭克福美茵河畔40樓上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24: | 川普刺激經濟三板斧:減稅加關稅棄環保 | |
| 2024: | 圖:西雅圖唐人街瑪嘎連續兩天隨機斬8 | |
| 2023: | 最討厭邏輯不自洽、雙重標準的網絡蠢貨 | |
| 2023: | 哈佛的一次民調:美國還有希望嗎? | |
| 2022: | 從參院選舉結果感覺川普2024沒什麼戲 | |
| 2022: | 中期選舉川普成最大輸家,共和黨將着手 | |
| 2021: | 告訴習近平主席,壓榨男人10年退休金是 | |
| 2021: | 告訴習近平主席,請共產黨憐憫弱勢男人 | |
| 2020: | 民主基石,公正不偏。 | |
| 2020: | 總統必勝之路官司很容易打到最高法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