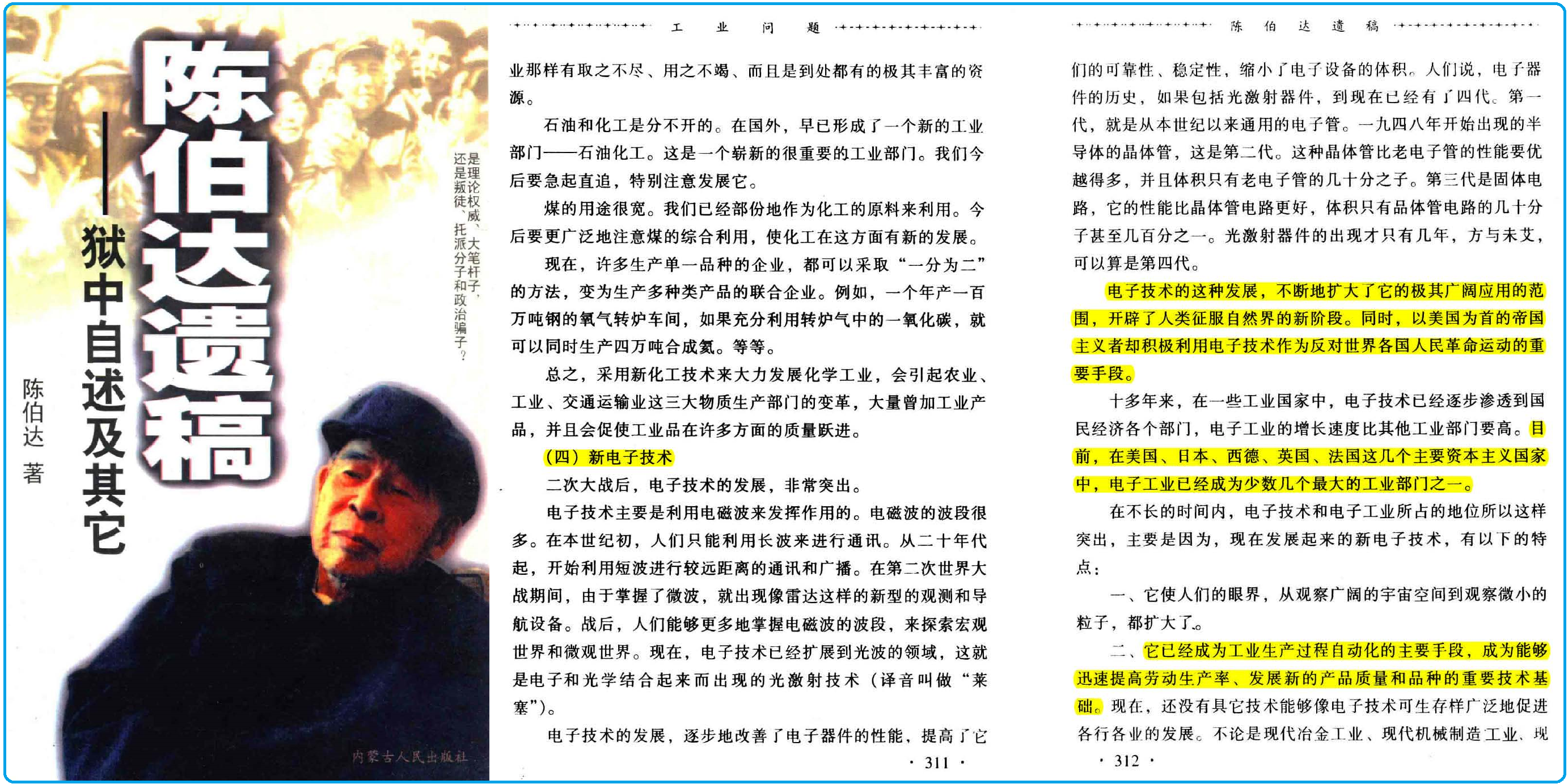| 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三:“指导”科学规划 |
| 送交者: 亦明_ 2022年07月16日09:54:0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三:“指导”科学规划
亦明
【提要】 据于光远本人及其拥趸说,于光远在1956年“领导”或者“指导”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本文通过大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于光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指导”科学规划的制定。恰恰相反,他留下的最大“科学”遗产,就是中国的电子工业的落后,至今仍会被美国“卡脖子”。
于光远荣登进士榜的第二年,1956年,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中极为罕见的祥和之年。相应地,这一年的于光远也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这是在他去世前半个月公布的《学术自传》中的话:
“1956年,我参与和指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担任该杂志的主编。我还参与并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议发言中阐明了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做了大会发言。1958年,我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提出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1962年,我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广州会议),这个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周恩来、陈毅等都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该会议从总体上重新判断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
于光远说自己“参与和指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并不是他在临死前给自己戴上的另一顶高帽,因为这个说法早已有之。1995年,与于光远和龚育之关系极为紧密、但其关系实质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马惠娣,就在一篇文章中说于光远“当年亲自参加《规划》制定与领导”。【2】而据马惠娣说,她的那篇论文曾得到于光远、龚育之等人的“悉心指教”。果然,于光远在次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参加第一个科学规划的经历》的文章,其中就有“张劲夫、范长江、杜润生、我几个人负责整个规划的框架结构、指导思想,即规划的总体设计,科学家们则按照总体设计分成若干组分头研究和编写”这样的话。【3】所以,到了2005年,连龚育之都这样说:“他参与和指导了一九五六年《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4】
上文已经证明,于光远在撰写“回忆”文章时,会给“史实”注入大量的水分。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衡量一下“我参与和指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这17个字的含水量到底几何。
一、事实、真相
所谓“十二年科学规划”,即中国政府在1956年上半年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制定的一项发展蓝图,其正式名称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5】尽管该计划从开始实施就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但它仍旧在1962年被宣布提前五年胜利完成。【6, p.313】半个世纪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熊卫民这样评论道:
“就12年规划而言,我看也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错。起点正确,然后运动不断,大错特错,转入正确的八字方针、十四条之后不久,又宣布12年规划提前完成、胜利结束了。受到那么多、那么大的干扰,我不知道它凭什么能够提前完成。如果只用1/10的预定力量就能完成那个规划,是不是那个规划本身订得很没水平?”【7】
而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的武衡,在多年后回忆那段往事时,专门写了一节“大跃进”,并且抄录了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天黑动手摘,半夜图纸好,黎明模型成,天亮实现了。”接着,他评论道:
“对科学技术如此轻蔑,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指日可待了。”【8, pp.178-179】
相应地,由武衡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书这样评价《十二年科学规划》:
“经过七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从十分落后的状况,大体上达到了国际上四十年代的水平。”【9, p.106】
其实,不论那个远景规划是否有水平,以及它的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它们与于光远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1、来龙去脉
原来,中国的“计划科学”航帆,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张开。1950年8月27日,也就是在“第一次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10】1953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国家走入计划性阶段,科学亦随之。”【11, p.23】在当时,中科院东北分院更明确地提出了“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是有重点的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一主张。【12】紧接着,在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郭沫若检讨了中科院的官僚主义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计划性缺乏,亦未抓计划。”【11, p.48】几天后,在全院“反官僚主义大会”上,郭沫若再次检讨中科院“十大缺点”,而位列第一的就是“缺乏计划性”。【11, p.54】当时,中科院访苏代表团的“总任务”第一项就是“关于领导计划等问题”【11, p.34】,而钱三强在访苏归来之后汇报的要点之一也是苏联的“制定计划”【11, p.168】。所以,当苏联专家、中科院院长顾问柯夫达(Виктор Абрамович Ковда, 1904-1991)在1955年1月提交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13】之后,中科院马上行动起来,在2月份向国务院做汇报,在3月召开学部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予以讨论,在4月份向国务院送交正式报告,要求“立即着手进行”。【14】【15】同年6月2日,在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指出,“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规律,根据我国的现状,制定科学工作发展的长远规划和目前计划”。【16】八天后,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总决议》中,更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科学院应迅速拟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并在一年内提出草案;全国科学事业的规划亦应协同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高等教育部从速制定。全体学部委员应积极参加这些工作。”【17】
到了9月份,显然是等不及上级的指示,中科院自己动手,开始大张旗鼓地搞《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18】【19, p.57】在当时,尽管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明确指示,但周恩来后来透露,“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20】所以,在1956年1月5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写信,指示他这个规划必须是向科学和技术进军的规划,必须“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21】也就是说,迟至1956年年初,中国的“科学规划”工作仍旧是在中科院的领导下进行的。
可是,中共中央在1月14日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闭幕之际发出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22】也就是因为如此,科学规划工作急剧升格,改由国务院牵头来搞。结果,中科院的那个自作主张的规划就变成了“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很好的准备”【19, p.58】,或“成为后者的蓝本”【23, p.87】【24】。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专门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美国学者萨特迈尔(Richard P. Suttmeier)才会把它当作中国的国家科学规划。【25】
2、泄露天机
包括于光远本人的回忆在内,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于光远曾“参与”或“指导”了中科院的自然科学规划,尽管他当时确实肩负“管一管”中科院的职责。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对科学院的规划工作不甚了了,所以他才会在四十年后贬低柯夫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说什么“他是生物方面的专家,是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但他对工程方面的事不熟悉,科学院曾征求过关于制定远景计划的意见,他的想法没有拉扎林科积极,多少偏于保守。”【3】结果,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曾经亲历其实的薛攀皋的批评,说他“有失公允”。【26】其实,于光远只是不了解科学规划工作的原委而已,并不是要故意贬低柯夫达,抬高“工农速成学校”出身的拉扎林科。
于光远对科学规划工作的无知,还反映在他把“两弹一星的成功”当作那个规划使“科学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27】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来自周培源,因为早在1983年,周培源就说过这样的话: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这个宏大的科学技术规划在1962年就基本上提前完成了, 并为此后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科学技术上创造了条件, 开拓了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多方面的新技术的研究领域。”【28】
且不说“两弹一星”的成功都是在1962年——即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中央科学小组宣布“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前五年完成之日——之后,只说它们的发起,就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之前至少一年。【29】【30】【31】【32】实际上,按照何祚庥的说法,他与龚育之早在1954年就曾上书党中央,建议研制原子弹。【33】其实,谁都知道,即使中国当年没有“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的“两弹一星”也会如期“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颇像是“陪太子读书”,因为这个规划虽然确定了56项重大研究任务,但在它们之中,还有12项“重点任务”【8, pp.164-165】、重点之中,还有6项是重中之重,称为“紧急措施”,它们全都是围绕着原子弹研制计划以及后来的“两弹一星”工作而设置的【34】。这是何祚庥说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的重要成就是除了制定了56项重大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四项(又称为6项,即其中包括当时未公开的两项国防任务)紧急措施,亦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为什么会挑选出这6个项目?而且当时几乎是所有科学工作者都一致同意这6项是当时国家最为紧急需要的6个项目?钱学森同志可以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5】
根据竺可桢的日记,国家计委原定在1957年拨给中科院外汇两千八百万卢布,但高校系统则只得到六百万。经过力争,中科院的外汇额被减到一千四百万卢布,但那六个“紧急措施”就申请了将近一千八百万卢布。【36, pp.464-465】实际上,在科学院之外,“紧急措施”更是香饽饽:
“当时搞‘尖端’最时髦,各地都在那里‘上马’、‘五子登科’(即电子、原子、半导体、自动化、人造卫星),人力物力的浪费是难以计算的。‘重视’了‘尖端’,就忽视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当前的紧迫的科研任务,把人力物力都攻‘尖端’去了。”【8, p.202】
可想而知,其他研究项目只能喝粥,所以北大的傅鹰在《人民日报》上抱怨北大的图书馆连“我们时刻需要参考的”期刊都供应不及时。【37】而即使是倾全国之力,在接下来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六项紧急措施”的总结也相当谨慎:
“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半导体技术、自动控制、高分子化学和计算技术等新的专业和新的学科的研究试验,在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来,并有了重要进展。”【5, p.52】
并且,这个新规划的一个目标就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过关”、“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过关”、“切实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初步过关”【5, p.54】——用聂荣臻的话说就是“突破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关” 【6, p.314】显然,在于光远“参与和指导”的那个规划完成之后,这个“关”仍旧存在。
很可能还是因为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具体工作和内容一头雾水,于光远曾这样写道:
“在我们编制工作时,有几位知识面宽、主意多的科学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一位是钱三强,他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一位是钱伟长,他对许多工作能发表很好的意见;一位是钱学森,他从国外回来,对国外科学技术的信息了解得比较多;还有好几位,他们的工作范围不限于自己的本行,而是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提建议出主意。”【3】
“三钱”虽然在1956年名噪一时,但是,钱三强并没有参与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因为从1955年10月起,他就在苏联考察学习,直到1956年7月才回国,当时科学规划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因为早在6月初,郭沫若就已经对外宣布“从去年十二月开始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拟制工作,在六月份内就要基本上完成了。”【38】所以,虽然钱三强“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基本上没有在国内参加科学规划的活动”几成常识。【23, p.98】【39】实际上,就是因为对国内的科学规划工作近乎一无所知,钱三强才会在回国之后对张劲夫说自己“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这样的话: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40】
注:关于钱三强1956年从苏联回国的具体时间,樊洪业虽然说是在1956年7月【39】,但是没有给出出处。而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对这个问题也多次语焉不详。例如,他在《钱三强年谱》中说,1956年“夏秋”,钱三强“在苏联学习考察的‘热工实习团’科技人员先后回到物理研究所。”【41, p.125】;在《钱三强》中说,钱三强在1955年“10月他和彭桓武等率领30余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参加审查堆和器的初步设计,并组织人员对口学习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时间达半年之久”【42, pp.127-128】;在《钱三强传》中说,钱三强在这年7月“同刘杰等向周恩来汇报与苏谈判援建原子能工业情况。”【43, p.415】而竺可桢则在其日记中记载,钱三强原定1956年6月20日回国,但他在6月24日收到钱三强发自莫斯科的信;一个月后才见到钱三强。【36, p.348, p.360, p.376】另外,据钱皋韵的回忆,他在1956年7月回国,当时钱三强尚在苏联。【44】
总而言之,即使把钱三强在苏联时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远景规划”进行过审阅和论证都算做是他对科学规划的贡献,它们与钱学森对科学规划的贡献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问题是,曾经“参与和指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于光远,把根本就没有参与科学规划工作的钱三强列在“三钱”之首,完全是出于无知吗?当然不是。于光远在写出上面那段话之时,正是他对钱学森最为仇恨之际,因为就在那之前十年,在自己“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纪念会上,钱学森曾当着于光远众多拥趸的面,逼迫“于光远表示:人体特异功能可以看,也可以研究”。【45】而到了1996年,于光远把自己十年前出版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46】拿出来重新出版【47】,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向以钱学森为首的“伪科学”发起第N轮攻击。所以说,他故意把对十二年科学规划做出巨大贡献的钱学森——他的学识和素养,连苏联的那些院士都啧啧称赞【48】——放在“三钱”的末尾,突显其对后者的憎恨。
根据竺可桢1956年1月28日的日记,当时的分工原则是,“社会科学由宣传部负责搞,自然科学由三个学部。”【36, p.282】实际上,在1955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党组书记张稼夫曾多次向中央建议,建立主管科学研究的常设机构。【14】【19, p.53】显然,当时在中科院的领导层内有这样一种共识:中宣部对科学院的管控只是政治上的,在业务上,他们根本就无从置喙。难怪于光远在畅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显得是在隔靴搔痒。
二、如此“指导”
那么,在国务院接管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之后,于光远到底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看看这段话:
“1956年1月3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陈毅、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具体主持,召开了包括中央各部门、各有关高等院校和科学家的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决定,由范长江、张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等10人负责主持规划的制定。”【49】
这就是于光远说自己“参与和指导”的根据,也是马惠娣说于光远“当年亲自参加《规划》制定与领导”的根据。【2】【50】只不过是,他们二人都没有指出这样的事实:那个“十人小组”之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即使是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也只有武衡一人而已。据曾亲身参加那项工作的薛攀皋说:
“关于‘科学规划十人小组’的成员说法不一。现在已见之于报刊的完整名单是范长江、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等10人。但这肯定不是小组成立时的最初名单。据1955年12月24日小组第一次会议记录,出席的有范长江、于光远、刘杰、刘皑风、李登瀛、张国坚、周光春、武衡、崔义田、叶锋10人。从第二次会议起,张稼夫一直出席十人小组会议。1956年2月中起出席小组会议的先后增加了薛暮桥与谷牧两人。从3月起,张劲失、杜润生才参加十人小组的会。由此可见,在李富春副总理于1956年1月31日宣布成立‘科学规划十人小组’后,小组的成员随着工作进展,有过调整。至于最后的十人小组成员人数,是否严格地限制于10人,存疑。”【26】
薛攀皋显然没有留意当年的《人民日报》,因为在1956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有一则新华社日前发布的消息,题为《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其内容就是公布“科学规划委员会”35名成员名单,其中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委员中有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竺可桢等科学家。蹊跷的是,在委员会名单的末尾,还附有一份“副秘书长”名单,共12人:范长江、张稼夫、薛暮桥、刘皑风、谷牧、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徐运北、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由于这个“12副秘书长”名单(外加秘书长张劲夫)与官方公布的“10人小组”名单高度重合,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秘书处”就是所谓的“十人小组”。不过,更为蹊跷的是,这12名“副秘书长”中,只有范长江和张稼夫属于规划委员会的委员(秘书长张劲夫也是委员),其余则全都位于委员会的“编外”——所以于光远后来这样说:
“在国务院的系统中我是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做具体领导工作的一名小组成员。”【27】
据曾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专职秘书”的何志平回忆说:
“规划委秘书处建立起一个非常精干的机构,编制30人,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 专门准备了一个招待所,为参加编制规划工作的科学家做好食宿等服务工作”。【51】
“副秘书长”武衡后来也说:
“如果提出和确定任务主要由科学家和部门负责人负责的话,那么组织落实就落在10人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头上了。”【8, p.164】
也就是说,到了1956年2、3月间,于光远虽然在职务上从“第二组员”演变成为“第十一副秘书长”,但在职责上,他却根本“参与”不了——遑论“指导”——科学规划的具体工作,只是为那些直接进行科学规划的科学家提供服务,或者负责规划的落实,因为当时就有传言说,“现在科学家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等到过几年拿不出成绩时再跟他们算账。”【37】也就是因为如此,当被自己的学生问到那个十二年科学规划“当时谁负责”时,龚育之才会脱口说出“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是领导,张劲夫、范长江和杜润生都是具体负责人。”【52】显然,在龚育之的潜意识之中,不仅藏有“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这个冷嘲【53】,而且还藏有“于光远凭什么‘指导’科学规划”这个热讽。
如上所述,那个“十人小组”早在1955年12月就已成立,并且召开过一次会议。但到了1956年1月中旬,中科院的院长顾问拉扎连科却发现他们根本“领导”不了这个工作,于是鼓动张稼夫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请国家对如何领导这一工作加以考虑。”【26】这很可能就是“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的根本原因。事实是,在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那个“十人小组”用来交差的文件,题为《中国科学院十二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不过就是中科院先前搞得那个“十五年规划”的翻版而已。【54】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规划10人小组成员都任副秘书长”【55】、但绝大多数成员没有捞到“委员”名分的根本原因。这是杜润生回忆当初——显然是在1956年3月以后——的情况:
“我记得我们几个人第一次碰头研究,怎么搞这个规划啊,咱们几个人都不是科学家呀!怎么办呢?范长江对我说,‘老杜主意多,你先说。’我说,‘我是个刚犯错误的人,我害怕说错话。’他说,‘你不要怕,讲错也是内部矛盾。’于是,我就提了个意见。第一,先搞清楚什么是当代科技世界水平,选择什么突破点,然后研究追赶。大家同意后,就决定把每一个门类有名的科学家都找到,把所有学部委员(现改称科学院院士)都找到。然后,就按学科和部门讨论,让各家都各说各的意见。”【56】
这是竺可桢1956年3月16日的日记:
“这次工作实际从一月廿三号开始,原定一月底结束,以后展至二月底,但到今天才能提出。”【36, p.305】
武衡后来说:
“规划10人小组根据《指示》,决定规划工作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要求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部分别提出本部门的规划草案,于2月底以前完成。第二阶段从3 月份起,以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和审查。经6个月的努力,于8月份完成了‘规划草案’。”【8, p.162】
显然,真正的“规划”工作是在“第二阶段”;而在这一阶段,具体工作只能由相关学科的专家来完成——范长江就在小组会上宣布:三月份后,“领导方式以学部为中心”、“在学部领导下讨论订计划”。【26】而在那些科学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于光远后来的死敌钱学森:他任“综合组”的组长,而“综合组”的任务就是决定哪个项目能上,哪个不能上——这是何祚庥在爬上于光远“反伪”战车之前的回忆:
“在1955-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曾经制定过一个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规模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这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使我国事业走上生机勃勃的局面。规划自然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科技界的领导同志,如张稼夫、张劲夫,范长江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但是,这一规划所涉及的科学领域是太广泛了,收到了很多来自科技界的建议。怎样从这浩如烟海,头绪纷繁的多种多样的建议里面理出一个纲?这样的任务便交给了当时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负责评价、裁决、选择、推荐,确定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决策。当时由海外归来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同志任综合组的组长。有幸的是,当时我曾参与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后达半年之久,得聆学森同志许多教诲,并目睹学森同志怎样从科学技术的海洋中理出一个《纲要》。”【35】
据薛攀皋考证,先后至少有22名科学家曾经参加过综合组的会议,他们之中,有16人是学部委员。【26】而在当时,钱学森尚不是学部委员。也就是因为钱学森的作用太过耀眼,所以于光远在1996年不得不承认,钱学森是当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知识面宽、主意多的科学家”之一,只不过于光远把钱学森排在了他的清华同学钱三强之后。【3】
事实是,为了给12年规划中的“航天技术”项目提供“一点参考资料”,钱学森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航空技术的展望》一文。【57】同样,为了给他倡导的“导弹优先”项目做出解释,他又发表了《从飞机、导弹谈到控制它们》一文。【58】不仅如此,钱学森还在《工人日报》上介绍第二次产业革命【59】,在《人民日报》上介绍“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60】。显然,这样的工作,于光远不要说插手“指导”,他连插嘴评论的机会都没有。事实是,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张劲夫在回忆当年的规划工作时,根本就没有提到于光远做出了哪些贡献,倒是对后到的副秘书长杜润生赞不绝口。【56】显然,这也是龚育之在提到“具体负责人”时点杜润生的名但却不提于光远的原因。
三、扼杀“芯脏”
其实,没能遭到于光远的“指导”,很可能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得以成功的一个原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个规划虽然罗列了五十多个项目,但其中却有六项“紧急措施”,即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机、导弹、原子弹——因为后两项属于保密项目,所以又称“四项紧急措施”。【34】显然,无论是六项还是四项,电子学都是头一项,因为没有电子学为基础,其他项目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早在五十年代初,钱三强就要把创建中的电子学研究所揽到自己的旗下。【41, p.104】而于光远恰恰对电子学颇有不屑——这是他在九十年代为了炫耀自己比陈伯达高明而讲的故事: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那时我和张劲夫兼任了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科委党组成员。有一天陈伯达把张劲夫找去(陈伯达那时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说,他考虑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改动一个字,改成‘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讨论一下,听听党组各位同志的意见。
“在一次党组会上,张劲夫转达了陈伯达这个要求。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要大家发言。结果会上谁也不讲,连张劲夫本人也没有发言,只有我讲了这么几句:‘列宁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建成共产主义依靠两条,一是要靠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一是要靠高度的社会生产力。在当时列宁所理解的最高的社会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因此列宁提出了那样一个公式。现在看来当然不再是这样,因此原则上可以改。我认为全国电子化这一条很重要,通讯靠它,许许多多新工艺靠它,生产自动化也靠它。但是现代的技术中还有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等等,用‘电子化’三个字还不足以全部概括新技术的发展。”【61】
尽管陈伯达的“全国电子化”建议刚刚诞生就惨死在于光远的手中,但陈伯达对此却念念不忘,多年之后,他深感惋惜地回忆道:
“完成了《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等文件以后,我开始搞工业方面的调查。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我先后到过北京、天津的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后来又去过东北的大庆油田和西南的攀枝花等地。我找科学院的负责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和研究人员座谈,探讨工业生产和科研中带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在调查中听取了一些科研人员的意见,有位从日本回来的技术员提出的意见很重要,他的名字我现有记不起来了。
“解放后,我国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在管理上,很多东西是抄苏联的,脱离中国实际。尤其是六十年代后,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大力发展电子技术,我们对此却比较迟钝,没有认识到电子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所以,我提出了‘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我几次和科学院负责人谈这个问题,有几篇讲话稿还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有过批语。
“那时候,钱学森、吴有训、叶渚沛等科学家都赞成我的意见,但是科学院也有个别人,如于光远同志,就不大赞成,说单提电子技术不全面,还应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其实,提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并没有排斥其他技术的意思。问题是当时没有一种其他技术能像电子技术这样快速地大规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广泛地影响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电子技术上不去,所谓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都将是一句空话。
“从1963年开始,我主持起草了个题目为《工业问题》的文件,因为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走向,为了慎重,四易其稿,到1965年夏天才定稿。当时,还考虑到于光远等人有不同意见,文件在强调发展电子技术的同时,也特别讲了其他新技术,而且没有使用‘电子中心’这个词,但是突出电子技术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我认为,于光远反对突出电子技术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站不住的。当年于光远认为新能源、新材料应和电子技术并列。其实,他所说的新能源,主要是指核能,所说的新材料,当时主要是指塑料。核能的利用也是需要的,但是核能在技术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核废料的处理至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至于塑料工业,塑料的确代替了一些木材和金属材料,但是塑料这种新材料也有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问题。总之,这类技术对工业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电子技术的影响却是全面的深远的。所以,只有重点抓电子技术,才是抓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他的技术也可能会超过电子技术。我不认为科学技术会总停留在一种状态上。但是在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电子技术确实在工业领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工业问题》的文件搞好后,我送交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特地请我一起吃饭。这是他解放后唯一的一次单独请我吃饭。席间,毛主席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
“过了几天,中央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参加会的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为是讨论我的文件,我也参加。讨论的时候,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因为‘以钢为纲’的方针是他采纳别人的意见,正式讲过的,现在也不好自己来否定。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我一看这种场面,心里很难过,就一句话也没说。会议就这样散了。”【62, pp.235-236】
文革期间,陈伯达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而对他的批判内容之一就是“电子中心论”。但即使是在批判“电子中心论”之际,那些批判者也不得不承认“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电子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其他工业部门有着广泛的应用性,它在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子技术是现代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建设的新技术之一”、“电子技术正在作为一门新技术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样的事实。【63】1976年,中国全年电视机的产量仅有二十多万台【64】,仅及罗马尼亚当年电视机产量的一半左右【65】。难怪当时的中国电视机市场先后被罗马尼亚和日本占领。最好笑的是,在当时,因为国产电视机质量太差,新华社竟然发出这样的消息:
“据第四机械工业部检查,我国黑白电视机的质量不好,主要是由于配套原件、器件特别是显像管的质量差,其次是由于装配工艺不佳,或没有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而总根源则是‘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66】
其实,与其把中国电视机产业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四人帮”,还不如归咎于于光远,因为在“四人帮”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已经死死地拖住了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后腿。
1983年,三联书店将美国作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28-2016)三年前出版的名著The Third Wave翻译出版,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今天,有四组相互关连的工业群,将有大发展的趋势,并且很可能成为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工业骨干,随之而引起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组合方面又一次出现大变动。
“电子学和计算机明显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工业群。从全世界看,电子产业问世比较晚,但现在每年销售额已达一千多亿美元,预计八十年代后期将达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甚至四千亿美元。这将使它成为仅次于钢铁,汽车,化学产业之后的第四大工业。”【67】
1987年,《参考消息》报道,东德首都柏林的最大工业部门就是“电子-电气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68】两年后,中国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学东写道:
“电子工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振兴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被认为是经济起飞的‘助推器’,军事力量的‘倍增器’,技术进步的‘催化剂’。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振兴,而且关系整个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国家的安危。电子技术水准,已被国际公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国防威力的主要标准之一。许多国家经济的振兴,都得力于电子工业的发展。美国靠发展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技术,保持了经济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日本通过振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跃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南朝鲜、巴西等国也采取了优先发展电子振兴经济的战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电子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工业跃居国民经济部门的前列。”【69】
到了1992年,把“机械电子”工业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终于变成了中国的国策。【70】这距离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又过了十年,“电子政务”被称为“一场深刻的革命”。【71】2018年,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而美方克敌制胜的两大利器,第一就是修筑关税壁垒,第二就是“直捅中国‘芯脏’”。【72】据分析,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子工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尚不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73】换句话说就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能够感受到于光远从坟墓中释放出来的“于光”——或者应该说是“死光”。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在这束“死光”的照耀下,方舟子在2006年对《21世纪经济导报》的记者大打出手,显然是要阻止他们对上海交大“汉芯”造假案的揭露——只是在这个企图失败之后,他才摆出一副“打假斗士”的模样,疯狂地抢摘“桃子”。【74】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纳粹对“中国芯脏”的仇恨和破坏持续了四十多年。
其实,一个人在六十年代意识不到电子工业的重要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于光远在二十世纪末对此好像仍旧意识不到,所以他才会把自己的“反陈业绩”——实乃劣迹——拿出来炫耀。而就是一个如此无知之人,竟然有可能“指导”中国的科学规划。这到底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画面?!
虎落平阳被犬欺,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在毛泽东麾下的“秀才”当中,虽然胡乔木是响当当的“一支笔”,但陈伯达却是实实在在的“点子王”。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陈伯达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陈伯达最先提出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称,也是他根据苏联历史上的“文化革命”改造出来的。实际上,连在中国走红了二三十年的“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也可能是陈伯达创造的,因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的,苏联的《真理报》就把农学家李森科称为“赤脚教授”。而在陈伯达提出的无数“点子”中,那个对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电子中心论”,却惨死在于光远之手;而在于光远的笔下,陈伯达永远都是一个窝窝囊囊、傻里傻气、卑微可笑的阿Q式人物。(图片来源:【75】。)
事实是,尽管于光远在文革后把陈伯达当作死老虎任意拳打脚踢,但在其一生中,他却从陈伯达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例如,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两句话: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76】
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77】
也就是说,八大决议中的那两句话是陈伯达写下的——陈伯达本人对此也“供认不讳”:“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我。”【62, p.131】而在1956年11月,于光远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其标题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78】,显然,这个标题就来自陈伯达的那两句话。让于光远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在一年后就否定了这个观点。【79】毛泽东的这个急转弯,打得于光远措手不及,所以他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马上来了一个急刹车——他在1958年出版的文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收录的文章全都是作于“1957年初”以前。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研究”还是“探索”,于光远的那双眼睛都一直在盯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并且随时根据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来调节自己的舌头和嘴巴。最好笑的是,到了后来,于光远一再强调自己一直主张“唯生产力论”。【80】而事实是,于光远连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学”都不允许,而是要他们另立门户,显然是因为他以为“政治经济学”要高于“生产力学”。【81】
四、蝇营狗苟
事实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其一生中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够与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相媲美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建议。实际上,经济学家于光远最著名的经济建议,除了把禹作敏的“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简化成“向钱看”之外【82】,就是因为“从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一位同志那里听到”的“介绍”而极力鼓吹“笼养苍蝇”。【83】【84】【85】你说中国人民花天价养活这样的大牌经济学家,专门靠道听途说——与陈伯达花两三年的工夫亲自搞调研完全不同——来给中国老百姓普及“穷办法”,是不是太不经济了?
最好笑的是,到了2005年,在给于光远九十寿辰祝寿之际,“万能”、“反伪”院士何祚庥把老恩公吹捧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而他举出的例子之一,就是于光远曾经倡导“苍蝇经济”,并且把它当作“这位‘大思想家’对人类活动的一次重大贡献!”:
“前一个月,我偶然地在中央电视台的科技频道上看到一位民营企业家因饲养苍蝇而发财致富的故事。因为苍蝇是高蛋白体,繁殖快,是极好的饲料,尤其是用来喂养鸡、鸭等家禽。但出人意外的是,在农村某地出现了鸡瘟,大部分的饲养的鸡,包括集中喂养和分散喂养的鸡,均遭到灭顶之灾,只有这位民营企业家用苍蝇喂养的鸡,却安然无恙。再一追查,原因在于苍蝇这种昆虫,长期和肮脏的垃圾打交道,长期处于各种细菌的包围之中,因而苍蝇自身就产生了能抵抗各种细菌的抗体。否则苍蝇将不能在生物圈里生存!现在人们用饲养中的苍蝇,来喂养家禽,就连同苍蝇所提供的蛋白质以及各种抗体进入鸡群,鸭群。所以就能在鸡瘟的袭击之下,仍然健康地成活成长!”【86】
上面这段话,在方舟子一手控制的新语丝上面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有人发帖子嘲笑道:
“何祚庥的苍蝇抗体论实在是妙[。]看来能不信口开河的人实在不多。”【87】
看到自己的老恩公在自己的菜园子遭到挤兑,方舟子脸上挂不住了,他跳出来为何祚庥狡辩道:
“许多昆虫(包括苍蝇)能分泌抗菌肽,能被用于做饲料添加剂[。] 何院士不过是把抗菌肽说成抗体而已。在说别人信口开河之前,最好先管管自己的嘴。”【88】
在新语丝上混的人都知道,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是方舟子的三大G点,一捅即喷。所以,有人或者是没能忍住,或者是故意挑逗方舟子,就这样接茬道:
“把抗菌肽说成抗体不算信口开河?‘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要‘根据斯大林发表的著作’来证明,何院士和光远同志都不愧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89】
这是方舟子喷出来的东西:
“何又不是学生物的,说错了术语有什么奇怪的?也不想想他们引用斯大林论述是什么年代的事。”【90】
让方舟子没有想到的是,那人不仅寸步不让,反倒得尺进尺:
“不是学生物的, 在信口开河前最好查一下[。]更何况不是学生物的, 也不应说出吃抗体长抗体这种笑话.相信50年代也没有几个科学家会引用斯大林来论述科学的阶级性, 更不谈今天还把它那出来当作学问大的证据.”【91】
方舟子的胀鼓鼓的舌头一下子就泄了气。第二天,他在新语丝“新到资料”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谭巧国”的文章,题为《对何祚庥院士文章的一处疑问》:
“我不是学生物的,只学过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就我所知,蛋白质(包括抗体)是大分子,进入消化系统后需要被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苍蝇所提供的蛋白质以及各种抗体’被鸡鸭吃进肚子以后,同样要被分解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就20种,并不会因为其来自抗体而有什么特别之处,应该发挥不了抗‘鸡瘟’的作用。这使我想起了方先生一直批判的核酸营养,感觉其中原理大概相似。方先生是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还望您能解答我的疑问。谢谢您!”【92】
这是方舟子在那篇文章的末尾给出的“方舟子答”:
“何先生说的抗体其实是小分子的抗菌肽,能够直接被肠道吸收。苍蝇等昆虫能分泌抗菌肽,可做为饲料添加剂通过口服进入体内发挥作用。”(同上。)
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那个“谭巧国”是方舟子随手给自己编织的一件新马甲。而为了给老恩公站台,方舟子竟然编造了一个“小分子的抗菌肽,能够直接被肠道吸收”因此能够“抗鸡瘟”的“科学原理”——看看他一年前“打假”“提高禽鸟免疫力的多肽饲料添加剂”时是怎么说的:
“你每天吃的蛋白质,在胃和小肠里先被蛋白酶水解成长短不一的多肽,最后被水解成氨基酸而被身体细胞吸收(有时小片段的肽也能被细胞吸收,那么它们将在细胞内被肽酶进一步分解成氨基酸)。”【93】
也就是说,科学纳粹的那张嘴,就是涂满了“苍蝇抗体”的肉窟窿,它们不仅能够抵抗“鸡瘟”、“鸭瘟”,还能抵抗全世界、全人类的所有“科学”。
中国科学纳粹中的女战士 在以于光远为领袖、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反伪(老头)帮中,有两名女成员,第一就是那个赤膊上阵的“女汉子”申振钰,另一个则是颇为隐秘的马惠娣。现在所有的信息都表明,马惠娣与于光远和龚育之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揭示这个“曾担任知识青年、工人、宣传干事”的人,是如何与于光远挂上钩以致“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所调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曾长期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主任、编审”【94】——实际上是内定的“主编”(Chief Editor)【95】——的;以及“1990-1993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94】科学管理的她,又是怎么摇身一变在2000年被“特聘到中国文化研究所,现担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94】的。据曾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刘梦溪在悼念龚育之的文章中说,“马惠娣近年致力休闲学的研究,五年前她来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休闲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她是龚育之介绍来的,原《自然辩证法》编辑部的工作仍继续。可以想见她和以自然辩证法名家的龚育之的渊源,以及和‘老少年’于光远的渊源。她开的休闲学的研讨会,光远、育之必来,我有时错位侧席,也是为了见到育之。”【96】至今,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官方网站,马惠娣的这个“研究中心”从来就不曾在其“机构设置”栏目中出现过。【97】马惠娣之所以引起“方学家”的注意,唯一原因就是她在兜售、推销方舟子时不遗余力:她不仅把方舟子托关系送来的稿子【98】发表在头版头条【99】,还把方舟子与人掐架的烂帖子也主动捡来,当作“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发表。【100】而据她自己说,《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最权威的哲学刊物之一”(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philosophy journal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95】上图为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 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一书封面、刘梦溪披露马惠娣与于光远、龚育之关系的文字,以及马惠娣与反伪帮大员在2005年的合影【101】。
|
|
|
|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复热帖 |
|
|
|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21: | “民主”走向“智主”最终走向无人智慧 | |
| 2021: | 科学研究的艺术 【附录】机遇在新发现 | |
| 2019: | 听拆字先生论哲学的定义 | |
| 2019: | 792、川普称習近平不再是哥們儿;场方 | |
| 2018: | 中国老教师考察美国后信仰崩塌 | |
| 2018: | 曜变天目茶碗(18) | |
| 2017: | 晓波死了,一丝游魂到了地府 | |
| 2017: | 浅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