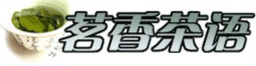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ZT:大林: 橘子花又開 |
| 送交者: 糍飯糕 2009月03月29日06:55:25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回 答: ZT:大林: 小狗堪堪 由 糍飯糕 於 2009-03-29 06:52:14 |
|
高鐵杆: 中國:奇蹟的黃昏 --- 袁劍 第六章 金融之劫(壞帳如虎)(3)
高鐵杆 回答: 中國:奇蹟的黃昏 --- 袁劍 第六章 金融之劫(壞帳如虎)(2) 由 高鐵杆 於 February 17, 2009 at 06:11:51: 四、流失的信用 中國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其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全能政治國家。只要行政當局願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系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裡,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一直被許多人固執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麼國家,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裡,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未來。那麼,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裡?他們究竟把壞帳藏到哪裡去了? 在我們看來,這大致有如下兩個出處。首先是財政。 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之間缺乏法律意義上的防火牆,幾乎完全是一體化的,財政可以向金融借錢,金融也可以向財政轉移債務,這種轉移只需要領導人的一個指示就可以達成。事實上,1998年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的2700億特別國債,就是金融壞帳轉變為國家財政負擔的一個明顯例子。而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的,名義上由資產管理公司承擔的幾萬億不良資產,最後的買單人也只能是國家財政。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隱性但卻是真實的財政負債。既然是負債,那就是要還的,既然要還,那就要看國家作為最後還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不管這些債務是對內(對國民的負債)還是對外負債。那麼,中國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儘管近年來,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出人意料的好,但這仍然掩蓋不了中國國家負債節節爬升的事實。粗略估計,如果將外債餘額、國債餘額、金融壞帳所導致的財政負債、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所引發的隱性負債包括在內,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7萬億左右,與2004年中國約13萬億的GDP總量相比,其比例達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統計的地方政府負債(包括大量的工資拖欠,政府工程項目拖欠、擔保或隱性擔保等等。有數據說,光鄉鎮一級地方政府的負債就達到6000億元左右[12]),這個比例還將提高。如此,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以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27000億元計算,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停發七年工資不說,所有的國防、教育開支也必須停止七年。幸好,這筆債務雖然要還,但可以分期還。(也不必還完,只需要保持比較安全的資產負債率即可)只要還這些債務還沒有那麼緊急,就不必讓所有的財政供養人員都齊齊去喝西北風。這就好像一個消費者按揭購房一樣,他可以將債務向未來推移,並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這筆債務。或者就像一家公司,只要該公司未來產生的收益可以逐漸償還這筆債務即可。不過,未來的畢竟是未來的收益,它並不是確定無疑的,而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按照有些學者的計算,中國可以估算國家財富和國家負債相比,已經在整體上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13])很容易引發償債危機。一個人如此,一個公司如此,一個國家亦復如此。即便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財政負債,中國的短期償債能力也相當不樂觀。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數據計算,中國當年的債務收入與當年的中央財政支出之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是83.9%和82.9%(?)。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25%~30%的安全線。換句話說,中央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依靠發債來維持。由於所有的國家債務都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後承擔者(這也是在一個非聯邦制的集權國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這個比例能夠準確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償債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發行大量國債來維持,中國短期償債能力的脆弱性實際上已經一清二楚。我們無法判斷中國長期的償債能力,但我們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對內的債務的償還高峰即將到來,理由是,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在一片中國奇蹟的喧囂聲中馬上就將不期而至,養老金及醫療保險將出現集中支付高峰。這一點,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期)引發對內債務的償還危機。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社會的景象將變得極其悽慘,吃不起飯,看不上病的黑暗歷史就很可能再現於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紀。(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經成為一種極其常見的現象。) 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金融壞帳的進一步打擊的。而已經發生的金融壞帳實際上盜竊了中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並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一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能夠立即造成切膚之痛的通貨膨脹相比,金融壞帳不痛不癢,卻悄悄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這可能才是金融壞帳的真正的兇險之處。壞帳並沒有消失,只不過,行政當局利用國家信用工具將它藏在了未來的某一處,隨時可能向我們發動致命的伏擊。由少數特定利益集團濫用、揮霍、盜竊全民財富所造成的壞帳,卻被行政當局慷慨地轉化為全民負債,在這裡,政府輕率地成為了這種野蠻剝奪的擔保者。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之所以可以這麼做,是因為人民不知情,是因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於無知、無奈或者發自內心的信任而給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所謂集權國家的效率)的時候,政府尤其應該慎獨、謹慎和負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已經無法撤銷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標準兌現它的改革承諾——不管這種承諾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嚴重的管制危機就將尾隨而至。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債務關係不像普通的債務關係,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這種關係中,政府既是契約的監督者也是契約的參與者,政府完全可以憑藉其壓倒性的地位賴掉這筆債務,或者乾脆否認契約(或者隱性契約)的存在。因為,沒有其他更強大的力量足以強制政府履行契約。其前提是,政府能夠經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損甚至瓦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基本的管制能力。當然,政府的信用越是減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這種難堪的情況,已經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演。在這個地方,政府的信用幾乎下降到了冰點。以至於投資者對政府包括最高領導人的任何信心喊話或者政策誘餌都變得無動於衷。對此,我們在本章開頭講述的那個悲慘故事的主人翁——下崗工人張小林,有着最銘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遺書中寫道:政府靠不住!這當然不止是信用的破產,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一個明顯徵兆。 除了利用未來的財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財政信用來隱藏壞帳之外,政府隱匿壞帳的另外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貨幣信用。主權國家有自主發行貨幣的權力,這為政府的貨幣遊戲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直接增發貨幣來隱匿、轉移壞帳就成為行政當局一件非常順手的辦法。在中央銀行完全缺乏獨立性的中國,這更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回顧一下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各種金融救助手段(注入央行向破產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其中相當部分都屬於這種貨幣遊戲。不過,央行雖然有憑空造錢的本領,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增加潛在或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而降低一國貨幣的信用。說到底,這是個有點蒙人,有點欺負老百姓智力的遊戲。我們曾經多次引用的一個數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窺測到中國貨幣體系中潛藏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6月末,衡量金融風險的常用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200%,這是中國創造的又一個反常的世界第一,接近美國同一指標的三倍。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仍然到處都充斥着“流動資金”短缺的喊聲。可見,中國的貨幣增長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根據這種趨勢,中國的央行官員戴根有曾經預測:如果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按8%增長,那麼10年後,中國M2/GDP為400%。對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許的最嚴重語氣警告:這個比例在世界金融歷史上都是從未見到過的!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貨幣體系中存在着奔騰性的通脹動力。中國的貨幣信用已經遭到嚴重侵蝕,人民幣可能面臨劇烈的對內貶值壓力。從傳統上說,通貨膨脹(通過侵蝕銀行負債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歷來就是行政當局解決金融壞帳的最後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當然,它也是最殘酷的辦法。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年(那時他還在擔任中國建設銀行的行長)曾經以憂鬱的口吻談到過。不過,他將這種辦法列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做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如果我們將這幾年急速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計入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那麼,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情況可能已經相當嚴重。這是不是意味着周小川所說的“萬不得已”的辦法已經在悄悄起步呢?我們不得而知。唯一可以明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信用會進一步流失。 無論是財政信用也好,還是貨幣信用也罷,政府轉移金融壞帳的辦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為代價的。在中國這樣的非法治國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過憲法契約及法律來實施的,而是通過它在國民中的信用來實施的,或者說,政府是通過允諾某種合意的未來而與國民達成的一種隱性契約來管制的。所以,當這個“未來”還沒有被充分“呈現”出來,或者政府的信用還沒有被透支完畢之前,政府依然能夠實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過“信用”工具左騰右挪,將風險轉移到未來或轉嫁、分散給國民。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金融現狀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過,一旦信用被透支完畢,或者“未來”低於人們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麼,被背叛的憤怒就會直接轉化為政府的管制危機。在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與政府管制危機之間,沒有任何防火牆。相反,只要任何一處有裂口被打開,他們之間就可能相互激盪,形成驟然放大的正反饋效應,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現存的秩序。這當然是金融危機,但也是一個剛性的全能體制被徹底耗盡之後的全面崩解。需要進一步指明的是,當中央政府壟斷了全部信用資源,掌握了最終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權力,因而也就對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契約擔負最終的履約責任的時候,所有的風險都高度匯聚於中央政府,換言之,中央政府將是這種危機當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也將是最脆弱的一環。從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所有的債務及最終的擔保責任都集於中央政府一身。 有趣的是,在中國對內債務高懸,信用流失嚴重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信用卻保持了相當良好的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給予中國“正面”評級的時候,它的一位評級專家多少有些困訝異地表示:中國目前的主權信用評級對於一個人均產值僅為一千美元左右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高的。他解釋說,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外債水平不高。的確,與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中國2286多億美元(2004年)的外債規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長期的貿易順差紀錄看上去也很讓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國對外贏得高信用評級多少是以對內信用的下降為代價的。這裡面存在某種不易察覺的替代關係。高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贏取了強大的對外形象,但卻大大增加了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從外部輸入通脹);類似饋贈的外資優惠政策雖然贏得了節節增加的FDI(外國直接投資),但卻廉價輸出了土地、勞力、稅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從國際社會極力爭取到的那種並不牢靠的恭維和主權信用,是以損害本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攘內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才具備。當然,它符合中國在外部世界一貫推行的“形象戰略”——維持並推銷一個強大的外部形象,並同時借外國人之口將這種形象“出口轉內銷”以增加合法性資源。 近些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在中國獲得了有力的傳播和廣泛的喝彩,這對亢奮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大的安慰。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對內債台高築、信用嚴重流失的現狀,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從長期看,人民幣有巨大的貶值空間,不管在短期內我們可以用優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機資金的追捧。對內的信用不存,對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長期堅挺的。對內信用是脆弱的,對外信用也註定是脆弱的,無論中國在“面子工程”上有多麼悠久的傳統,是多麼優秀的行家裡手,恐怕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常識。在我們已經觀察過到金融危機中,危機的原因從來就是來自內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存續和經濟增長的必備的基礎設施,在中國轉軌時期,它是由政府壟斷並由政府注入市場體系的,這既保證了政府主導型的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信用嚴重的透支和濫用。如果將金融信用看作一種公共產品的話,那麼,我們顯然已經在中國看到了一場典型的公共產品的災難。在未來,這種災難完全可能轉換為政府治理的災難,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最險惡的敵人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們很難與大多數專家們一起保持同樣的樂觀。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金融危機會在何時發生,我們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場標準意義上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確認的僅僅是:金融已經為一次“大爆炸”式的體制斷裂準備了充足的彈藥。 五、困局與賭注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嘗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一輪大規模注資之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一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一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滙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後,滙豐的所謂技術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一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一輪的開放歷史中,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一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似乎並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有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多少提升。當然,老外不願以“教”只是一個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制不鼓勵“學”,對此,一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實際上,對中國金融業來說,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品並非那麼神秘,也遠非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幾個諮詢公司三拳兩腿就可以將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時髦女郎”的事實說明,先進管理和技術離中國國有銀行實際並不遙遠,顯然,中國國有銀行的關鍵隱患並不在缺乏管理和技術,而是在別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彙。頗有一點“一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一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一種場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一種文化投影和複製。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複製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在中國金融企業中一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許先生斷言:“……只要外資進入,就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打破現有的關係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實上,究竟是外資銀行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銀行的行為,還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同化外資銀行的行為,還遠遠是一個不確定的結論。在這一點上,許小年所表達的與其說是一種推理,不如說是一種期望。跨國公司在中國不斷捲入商業賄賂的事實暗示,許小年的這種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以來的一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國改革問題的一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一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癥結。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一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一個隱含的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藉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於倒懸,恐怕只能是一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聲掃地的國企改革,只不過,老闆換成了老外。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症”),中國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後於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後果,已經在廣大範圍內尖銳的地呈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於這塊生鏽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一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僅是開始。箇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之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一點麵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這種後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一種後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裡,任何僥倖的假設都沒有存身之地。 從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着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一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壞帳轉移地)。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一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中的凋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投機性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一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遊戲中,中國除了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一場博弈中就輸得一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注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一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一幅陰鬱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後果並非是小概率事件。對於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一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一來是因為他們與國際資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後一年。大限一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畢其功於一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着一場生死豪賭。不幸的是,這是一場並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http://www.5lake4sea.com/forum/dongting/upload/301667_2.JPG http://www.5lake4sea.com/forum/dongting/upload/301667_3.JPG http://www.5lake4sea.com/forum/dongting/upload/301667_4.JPG http://www.5lake4sea.com/forum/dongting/upload/301667_5.JPG |
|
|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復熱帖 |
|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8: | 唯色:8年前的預言,來年還將重演(圖) | |
| 2008: | 轉貼: 美國為什麼一定要“送錯”武器? | |
| 2007: | 也談《圍城》vs《京華煙雲》 | |
| 2007: | 司馬非馬:《最後的刺客》(30) | |
| 2006: | 神州大地鴨幾多--中國男人賣淫現狀 | |
| 2006: | 作為中國文人搖頭丸的偽藝術 | |
| 2005: | 血緣:第十四章 多少愛無根無脈 (4) | |
| 2005: | 各種版本的小寡婦上墳 | |
| 2004: | 你又飛走了 | |
| 2004: | 仍然想念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