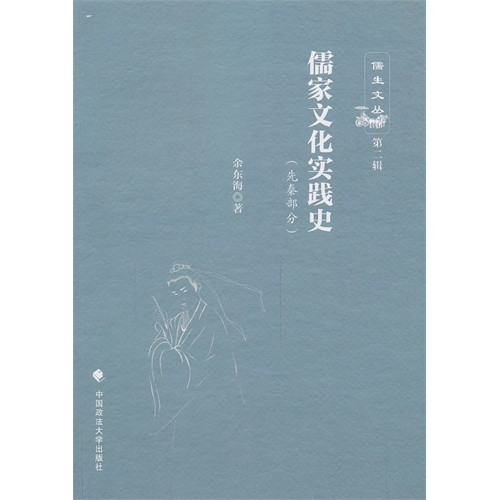| 秦法家的下場 |
| 送交者: 余東海 2020年12月23日02:07:0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
秦法家的下場 —兼論“惡必蠢”律 一
世俗以成敗論英雄,儒家以道德為標準。俗話說成者王侯敗者寇。其實寇無論成敗永遠是寇,成了王侯甚至得了天下如秦始皇,依然是寇。或說“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這是假話,歷史上從來沒有“講秦始皇好”的一派。這一派是在五四以後價值觀嚴重混亂顛倒後才出現的。
政治和制度之惡是人世間最大的罪惡。秦始皇極權暴政,罪惡滔天,焚書坑儒,影響惡劣。“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焚書運動,和繼之而來的項羽火焚阿房宮一起,對中國古文化造成毀滅性的空前破壞。同時,秦氏模式的統一,也是歷史性的倒退和犯罪。(理由詳見東海《君主制之思---兼論統一的模式和善惡的傳染性》一文,那是本文的姊妹篇。)
秦始皇自己身死野外,罪有應得,秦氏家族被滅族,勢所必然。多數作為幫凶的文臣武將,或死於非命或被趙高秦二世滅族,也是咎由自取。
古人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飛鳥狡兔尚多的時候,呂不韋這張良弓和白起這頭走狗,就被秦家毀棄了。
秦始皇可以說是呂不韋一手“策劃”出來的。呂不韋,戰國末衛國濮陽人。原為大商人,在趙都邯鄲遇見入質於趙的秦公子異人,認為“其貨可居”,因入秦遊說華陽夫人,立異人為太子。秦莊襄王繼位,任為相國,封文信侯。秦莊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繼位,是為秦始皇。
呂不韋繼任相國,被尊為“仲父”。門下賓客三千,家僮萬人,匯編了傳世巨著《呂氏春秋》。他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併六國有重大貢獻。後因嫪毐集團叛亂事受牽連,被免除相邦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復命讓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鴆而死。呂不韋是雜家,並非法家,但他“策劃”和成就了秦始皇,落此下場也不冤枉。
白起,羋姓,白氏,名起,楚白公勝之後,故又稱公孫起。戰國四將之一(其他三人分別是王翦、廉頗、李牧),白起指揮許多重要戰役,大小70餘戰,沒有敗績,殺人如麻,號稱“人屠”。
綜《資治通鑑》所述,武安君白起一生拔城八十六座,殺人一百餘萬:長平之戰共殺人四十五萬,連同以前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攻楚於鄢決水灌城淹死數十萬,攻魏於華陽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於陘城斬首五萬…這是一張很不完全的白起殺人賬單。據梁啓超考證,整個戰國期間共戰死兩百萬人,白起據二分之一。
《史記白起列傳》介紹了白起被秦昭王逼迫自殺的故事,茲不詳說。臨死前白起承認自己該死。“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二 秦氏王族中,最優秀的人物是太子扶蘇。他與秦始皇相比,頗有遠見,略為寬容 因多次勸諫秦始皇和反對坑儒而被外放,“北監蒙恬於上郡”。世人都以為扶蘇有仁德,甚至有學者認為扶蘇是儒家。其實扶蘇雖持政治異議,與秦始皇的極權立場和本質並無不同,父子矛盾,屬於秦法家內部“兩條路線”之爭。
關於這位太子的資料太少,但從兩點足以論定他絕非儒家---最多只能說他對儒家有些同情。他對秦始皇的諫語是: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蘇反對坑儒的原因,一是“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民心不穩;二是“諸生皆誦法孔子”,繩以重法,怕引起天下不安。都是為極權利益考慮。
如果說這是諫術---面對秦始皇不能不這麼說,那麼,扶蘇的自殺則是毫不負責任、毫無儒家味的。他開發秦二世使者帶去的書信後即欲自殺。《史記-李斯列傳》載: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蒙恬說得很有道理,可是扶蘇不聽,還是自殺了,司馬遷說“扶蘇為人仁”。按照儒家標準,扶蘇這麼做,既不孝也不仁,對家國、對父親和自己都是不負責任的,太也懦弱愚蠢,死得輕如鴻毛。後世“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邪說,與扶蘇“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這個說法,可謂一脈相承。
對於父親,儒家有“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之說。象舜的做法才是正確的。“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下過,則受罪。”(《史記》)
叢林性和逆淘汰,是極權社會的特徵,極權政治內部同樣有此特徵,甚至變本加厲,對善良零容忍。扶蘇被外放和被賜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扶蘇素有賢名,後來陳勝吳廣起事反秦時,因天下尚不知扶蘇冤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易通達),就曾偽稱“公子扶蘇”起兵,作為號召。
三 秦始皇本人對秦氏貴族和多數文臣武將雖刻薄,畢竟沒有大規模迫害誅殺,趙高和秦二世可就不一樣了。秦二世在趙高的謀劃、李斯的配合下登了基,擔心朝中大臣和各地官吏不服,諸兄弟與他爭位,悄悄與趙高商議。趙高給他出了個主意:
“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秦二世非常贊成,乃更改法律,在原來嚴刑峻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嚴峻化,指令趙高對包括蒙恬蒙毅兄弟在內的文臣武將和秦族公子大開殺戒,“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準備逃跑,又恐家屬被族,只好上書,請求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請求,公子將閭昆弟3人,被迫自刎。據專家考證,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全部死於非命,而且多死在胡亥手裡。
陳勝吳廣起義後,天下大亂。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勸秦二世停止營建阿房宮和減少四邊戍卒轉運。秦二世把他們交給執法之吏追究罪責。 去疾、馮劫倒頗有志氣,說“將相不辱”,自殺了。
李斯被囚,二世二年七月被腰斬咸陽市。臨刑前,李斯回頭對與他一起被抓的中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相對痛哭,被夷滅三族。
李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那種文人中最壞的壞種,完全不值得同情。僅憑其焚書坑儒的建議,便是難逃天譴的大惡。陳勝吳廣起義後,各地風起雲湧,秦二世很不高興,多次嘲笑指責李斯,李斯恐懼,貪重爵祿,於是順從二世的意思,上書建議秦二世“行督責之術”,“滅仁義之途,絕諫說之辯”, 獨斷於上,“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史記》)
這封上書全是喪心病狂之言。但秦二世高興地採納了,“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這樣一來,秦民益駭懼思亂了。
很快,秦二世也被趙高幹掉了。其實,秦二世若有正常人的智力,在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就該提高警惕了。可是他直到臨死前,對趙高仍毫無懷疑。趙高精心設計了一場宮廷政變,命令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去殺秦二世。知道是丞相(趙高)所為後,他還傻乎乎地提出一個又一個要求。《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是描述:
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原為萬戶侯。”弗許。曰:“原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秦二世與趙高勾結,為了奪權叛父殺兄,為了維權又大規模屠殺秦家兄弟(諸公子)和文武老臣,殘忍兇惡,做了三年傀儡皇帝,最後死於他最信任的趙高之手,可謂死得其所。如果死於別人,未免對不起他。
趙高殺秦二世後,立二世之兄子子嬰為秦王。之所以不稱帝,是趙高認為當時六國各各自立,秦地越來越小,不可以空名為帝。沒幾天,子嬰刺殺了趙高,並且“三族高家以徇咸陽”,滅了高家三族。
子嬰當秦王四十六天,劉邦破秦軍入武關,派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系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一個月後,諸侯聯軍結集,項籍是聯軍的秘書長,殺了子嬰,滅了秦族。秦氏貴族享受了秦始皇統一帶來的短暫的榮華後,都高度一致地付出了生命代價。
秦孝公以來,無數人為秦氏王朝的統一事業奉獻了生命,無數人主動或被迫、直接或間接地充當了秦始皇的幫凶,而被秦王朝直接害死的中小型幫凶無數無量。如秦王陵大大小小的監工,最後都與無數工匠一起被滅了口。據《史記》載:“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秦始皇本紀》)
《史記》載,趙高在動員李斯與他合謀另立胡亥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可見,歷代秦王朝都刻薄寡恩,被免職和罷去的丞相功臣,“皆以誅亡”,都沒有好下場。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黑暗的深淵裡沒有贏家,一個也沒有。文化邪惡和政治罪惡共同製造了這一段玉石俱焚的歷史黑暗,空前而不絕後,後繼有人。
四 說秦法家,商鞅是無法避開的。商鞅是秦孝公的人,與秦始皇不同代,卻為秦始皇統一天下奠定了強大的軍事和思想基礎,屬於間接幫凶。關於商鞅,蘇軾《商鞅論》值得一看。
蘇軾先引《史記》的評說:“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然後加以否定:“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指責司馬遷把游士的“邪說詭論”當作信史寫進了《史記》。
蘇軾指出:“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
意謂秦國本就是天下強國,秦孝公也是有志君主,修其政治刑法十年,不為聲色犬馬遊樂腐敗,即使沒有商鞅也能富強。秦國的富強是秦孝公抓住根本發展生產的效果,不是商鞅流血刻骨的暴政之功。後來秦王朝遭到人民痛恨,就像痛恨豺狼虎豹和毒藥,一夫發難天下響應,秦亡國滅種,乃是商鞅造成的。
東海認為完全否定商鞅變法的效用,也是不公平的。不過,必須說明,這是烈性壯陽藥壯起來的“大”,這種強大是建立在濃濃血腥累累白骨之上的,危險重重。這不是功勞而是罪惡,而且後遺症極大。
很贊成蘇軾把司馬遷“論商鞅,桑弘羊之功”定為“大罪”。蘇軾認為漢武帝及後世某些帝王陽儒陰法,對商鞅和桑弘羊陽諱而陰用,與《史記》的影響不無關係。(說明一下,桑弘羊與商鞅有異,茲不詳論。)
東坡進一步指出,用商鞅之術,必然“導致滅國殘民覆族亡軀”的結果。世間君主們之所以樂於採納,是因為其術簡單便捷,便於“以天下適己”--讓天下人為自己服務,讓自己舒適,因此貪圖一時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東坡說: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所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商鞅推行反人道、反人性的嚴刑峻法,“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資治通鑑》卷二周紀二)最後作法自斃。
人並不是達到別的什麼目的的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這是中西良性學說的共識。儒家以仁為本,為最高目的,而仁是人的本質,肉體和意識作為現象,與仁是一體的。尊仁,必重人。而反儒就是反仁,也就是反常道、反人道、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
東海曾經提出一條鐵律:反儒必反常。反儒的政治必邪惡,反儒的社會必野蠻,反儒的時代必黑暗,反儒的勢力必反動,反儒的人物必有缺,不是缺德就是缺智。法家把人當作工具,嚴刑峻法,草菅人命,是因為認人之本性為惡,其原則錯誤和反儒思想深藏在其人性論中。正如蘇軾所說,採用商鞅之術,必定先要鄙薄和嘲笑堯舜禹湯。
五 法家的農戰政策、嚴刑峻法和戰時體制,與民為敵、防民如賊的治國方針,就像烈性壯陽藥,雖一時有效,但必然導致越來越強烈的反彈,不斷為自己製造敵人。
莊子說“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剋是克的異體,剋核即克核,苛責。不肖,不正、不善。過於苛責或逼迫,別人就會興起惡念報復。法家暴君暴政,可不僅僅“剋核太至”而已,製造大量暴民、遭到加倍回應是必然的!
防民如賊與民為敵,一定會變民為敵。“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德經》)民意比起川水來厲害多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得越久,潰得越凶,一旦破閘而出,將無堅不摧,天地變色。政權與民意,局部看政權是石頭,實質上民意才是石頭,政權只是雞蛋。暴秦的暴起暴亡,法家有“大功”焉,尤其是韓非。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式的人物。法家中,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韓非子將法術勢統一起來,為極權政治和獨裁者打造了一個完美的工具。
韓非子主張,君主應該擁有絕對權威,集天下大權於一身,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加君主極權的國家。還有,全民動員的農戰政策所帶來的短期效益,信賞必罰、連坐告奸所產生的輿控力量和君主權威,對於野心勃勃而急於功利的秦始皇,吸引力比任何學說都大。
韓非還為君主極權主義找到了形上依據。熊十力指出:“韓非主獨裁,主極權,其持論亦推本於道,故曰‘道不同於萬物’乃至‘君不同於群臣’,又雲‘道無雙,故曰一’,又雲‘明君貴獨道之容’,此則於本體論上尋得極權或獨裁之依據(熊十力《韓非子評論》)。
其實韓非的說法似是而非,割裂了形而上與形而下、即道與器的關係。道是“一”,不同於萬物,不錯,但更要知道,道不離乎萬物,道在萬物之中,離開萬物,便無道可言。易言之,這個“一”並非獨立於萬物之上,而是“一歸萬物”。
儒家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盡其責。法家則一味強調君威君權,臣民只是君主的工具,只有服從的義務。“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這是《韓非子》的開頭,邪惡之氣撲面而來。
儒家對法術勢和暴力並不一概反對。儒家刑法的嚴峻程度也很高,權道包括術勢,湯武革命就是暴力。唯儒家強調法本乎禮,權(權術)本乎經,力本乎義,一切以仁為本。法律也好暴力也好,都不允許擺脫道德的制約,掛帥的必須是道德。
法家錯就錯在違仁背義,滅德反智,唯崇法律和暴力,如韓非說:“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這三句話是韓非思想的根蒂,其一切知見、論證和主張,無不歸結於此。
韓非沒有機會為秦始皇所用,但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秦始皇。秦始皇初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他的學說得到了秦始皇的高度讚賞和深度實踐。統一之後焚書坑儒,雖出自李斯建議,皆本於韓非《五蠹》篇。韓非子無疑是秦政的文化幫凶。為老同學李斯所害,可謂天理昭昭,自作自受。“發明”、鼓吹和傳播歪理邪說,屬於大妄語業,報應很重。
韓非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的了解非常透徹,“政治智慧”頗為獨到,為君主考慮謀劃得萬般周到,在法家序列中其見識是最高的。《孤憤》說:“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以燭其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以矯其奸。”
可是,他未能明察、燭見李斯的陰險奸詐,終究智術有限。或說韓非是因為李斯是老同學才十分信任不予防範。殊不知韓非子主性惡論,認為人性難與為善,其書隨處把人當做壞物看,如防蛇蠍,如備虎狼,即使夫婦父子不足相信,何況同學?同學而不了解對方性情,盲目信任,終究是缺乏慧眼,缺乏知人之明。
或稱讚商鞅韓非李斯們是帝王師或帝王培訓師。大錯。伊尹傅說周公才是帝王師。韓非是政治盜賊、極權暴政的培訓師,商鞅李斯之流則是狗頭軍師,徹頭徹尾的賊奴,俗話說的狗奴才,《韓詩外傳》說的“國賊”。《韓詩外傳》說: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老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國師”是老師之師、君主之師和國家之師,責任更加重大,更應該傳真道授正業解各種迷惑。如果“國師”傳歪門邪道、授魔鬼之業、增世人之惑,惡果特別嚴重,罪業和果報也特別大。商鞅韓非李斯們的下場就是證明。他們培養和引導出來的政權和政府,堪稱當時天字第一號的恐怖組織犯罪集團。
法家邪說暴政毀人不倦,既毀害他人、毀壞社會也毀滅自己。在野蠻的叢林,法家實踐或可收一時速效;隨着全球性的文明發展,文明正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 這類邪說的實踐效果會越來越差,而自身毀滅的速度則越來越快。
六 愛好欺詐擅長騙人者,時間一久,也會把自己蒙蔽了,置身於火山之上,還自以為穩如泰山,自以為可以永遠一手遮天,東方不敗。法家大腕們當然都很精於算計擅於鑽營,可是,終究是小處聰明大處愚蠢,表面聰明本質愚蠢。蘇格拉底說過:聰明與智慧的區別就在於智慧中還含有美德。然哉然哉,中西同然。
由於迷信權力、暴力和陰謀詭計,被權力暴力消化了智力,被邪知邪見陰謀詭計遮蔽了智慧。普通人都能預料的後果或能看見的危險,法家大腕們往往視而不見。商鞅以他的刻薄暴虐和嚴刑惡法,把自己變成秦國的全民公敵,從貴族到平民,無不恨之入骨。臨死前五個月,門客趙良已經直言指出其危若朝露的處境: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史記》)
趙良之言,至今讀來依然字字驚心,給商鞅出的主意,也屬對症之藥,可是商鞅就是無動於衷,不肯聽從。如果是防不勝防倒也罷了,商鞅是不作任何防備工作,狡兔三窟,他一窟也沒有(封地商屬於秦國,隨時可能被收回,而且地狹人少,人心不附,毫無安全可言。)而依舊驕橫貪財獨斷專行耀武揚威。商鞅一再強調“民弱國強,民強國弱”,鐵血推行“弱民”政策,自己也變成了弱智。不到半年,秦孝公去世,他就大難臨頭了。
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門下有人指控商鞅謀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商鞅逃往深受其害、深受其騙的魏國,當然被拒納,還把他送回秦國。商鞅只好與他的門徒來到封地商於,起兵北攻鄭縣。秦軍進攻商鞅,將他車裂分屍,盡滅其家。《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新序》說: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
更加愚蠢的是趙高。王夫之說: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
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弒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為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閒,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袽,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讀通鑑論》)
小人都是利益主義、利己主義者,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置個人利益於他人、社會、國家和一切之上。但在關鍵時刻,小人往往犯糊塗,不僅違反道義,也違背利益和安全兩大原則,暗暗算計他人,明明坑害自己。在旁觀者眼裡,簡直莫名其妙愚不可及。
象趙高,任何人都萬萬料不到他會作出“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這種決定的。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看得出來,這麼做與自殘自儘自己找死無異。“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因此,小人之心,愚者不能料,智者亦弗能測。聰明起來了不得,愚蠢起來更不得了。當局者迷,迷到趙高這種程度,驚天地泣鬼神啊。
曹劌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東海曰:惡人必鄙,必無遠謀。秦始皇號稱雄才大略,其實毫無知人之明,越老越糊塗,居然信任趙高、李斯這種人,給他們託孤托國,還奢望什麼千秋萬世,活該秦朝二世而亡,秦家絕嗣滅族。當然,除了趙高李斯輩,他也無人可托。法家朝廷上本來君子罕見,經過焚書坑儒,就更難求了。賈誼在《過秦論下》曾分析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說: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
“秦王足已而下問,遂過而不變”,不就是愚蠢嗎。雄才大略云乎哉。
注意:法家有兩種,一種是重道德的法家,如管子,“假仁假義”,導出的是霸道政治;一種是反道德的法家,即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的秦法家,違仁悖義,導出極權暴政。這一種法家才是法家之正宗。
七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從智伯滅亡的故事開始。他深刻指出:“智伯之亡,才勝德也。”、“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商鞅李斯秦始皇這些法家大腕,不僅僅“才有餘而德不足”,而是滅盡良知缺了大德,覆家滅族和滅國是必然的。
崇拜暴力及陰謀權術者亡於暴力及陰謀權術,人禍的製造者必遭惡報,必有大禍,不禍發自身,必貽於後嗣。這就是報應,這就是天理的公道。最令人感嘆的是,多數秦法家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真可謂惡人自有惡人滅。
把眼光拉長,人類有史以來,凡是大惡大凶,無不下場悲慘,絕嗣滅族者史不絕書。黃巢張獻忠洪秀全之類盜賊或絕嗣或滅族,桀紂隋煬帝之流暴君家破國亡死於非命,西方也一樣,希特勒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雖然猖狂一時,最後無不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歷史的教訓何其深刻,歷史的經驗有待吸取啊。
從世俗角度看,他們哪一個不是聰明絕頂才智超群的?他們對自己的聰明才智也無不自信滿滿,自以為可以“與天斗”與歷史規律斗,可以不受因果律的制約。實質上都是蠢材。
秦法家及其幫凶的命運和下場證明了兩個定律:惡必蠢和惡必苦。
惡必蠢。邪惡之人都有小聰明而無大智慧,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惡的程度越高時間越久,越蠢,下場越悲慘。
惡必苦。邪惡之人,縱有表面榮華,必然心靈悽苦,縱然一時輝煌,難免下場悲慘淒涼。所謂占小便宜吃大虧,虧心,喪心,最後喪命。相對生命的寶貴和良知的高貴,一時的榮華富貴,仍不過小便宜而已。他們就像賭徒,無不小贏大輸,輸掉的往往是自己的性命,甚至整個家族和子孫後代。
還可以延伸出另外兩個定律:惡必丑和惡必偽。
惡必丑。劇毒的花朵或許嬌艷,邪惡的東西(包括人物事物)必然醜陋。俗話說:三十歲之前的容貌父母負責,三十歲之後的容貌自己負責,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少時英俊,越大越丑,與其心靈的惡化密切相關。牟宗三說過:現代中國人是有史以來最醜陋的(大意)。這種醜陋,包括品德和容貌。
惡必偽。誠的境界極高,小人望塵莫及,何況惡者。古今中外所有邪惡人物和勢力一定虛偽,一定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一定要搞陰謀詭計耍鬼蜮伎倆,一定有很多見不得人的秘密。
四個定律從負面證明着良知律。一、快樂是良知四德之一。(良知四德:常樂我淨。)良知泯滅,內在的平安喜樂亦不可能;二、良知是大德也是大智,是德智的高度統一。喪心必然病狂,缺德必然缺智。“惡必蠢”倒過來也成立:蠢必惡。良知知是知非,只要是人,即使沒受過教育沒有知識,也不可能完全分不清基本的是非善惡。如愚蠢到崇拜秦始皇及其幫凶們的程度,必非良善,必缺德喪心。
三、真善美,三合一。良知至善至真,也是至美大美;四、《中庸》認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這個誠,就是良知本性。其實,因果循環和善惡報應,就是良知律的體現。良知律告訴我們:
惡沒有贏家。通過損害他人和社會利己,通過惡的手段和方式獲得到的“東西”, 無論是利益,特權還是政權,都是脆而不堅、堅而不久的,最終害了自己。
善才能雙贏。儒家內聖外王,正是雙贏、多贏之學。內聖盡己之性,是自立自達和成己,成就自己良知輝煌;外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是立人達人成人成物,成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多層次全方位的和諧。成己和成人成物,相輔相成,聖王不二,內外一體,雙贏多贏,統歸於仁。而反儒的學說、人物和勢力,罪惡極大,惡報也極大。這是被歷史和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余東海2012-4-20 於南寧 本文選自於東海儒書《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18: | 聯想柳傳志:資本炒作阻礙科技發展 | |
| 2018: | 解“真”——幻與真,真與偽,真與假 | |
| 2017: | Introduction to Instancology(-2):Bac | |
| 2017: | 陰暗的心理,陰暗的審美,陰暗的芳華 | |
| 2016: | 我讀書多你不要欺負我 (一) | |
| 2016: | 這個人類起源故事至少不比學校教的進化 | |
| 2015: | 老天爺的采詩官檳郎 | |
| 2015: | 太陽系是人造的證明推導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