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利會 知識分子 Yeste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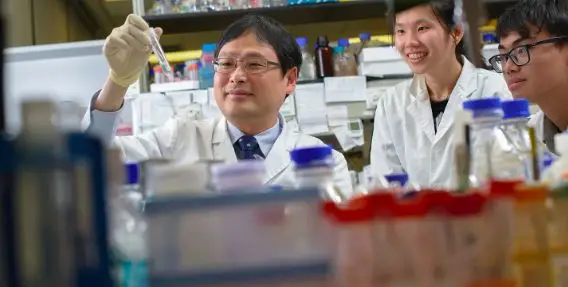 作為長期跟病毒打交道的人,病毒學家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熟悉病毒的那群人,病毒如何發生,如何傳染,疫情如何發展,如何防護,病毒學家都應該有話可說。在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金冬雁看來,武漢這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應對有諸多可商榷之處,他說,作為病毒學家,最重要的是和公眾坦誠交流。12月31日、1月3日、5日、11日,武漢市衛健委稱,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沒有醫務者感染;1月15日,武漢市衛健委稱, “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表示, “根據目前的資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傳人”;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宣布 “封城”。連日來,面對蜂擁而至的求醫者,醫療物資的短缺,促使武漢各大醫院紛紛發起了募捐活動,與此同時,軍隊醫院、上海、廣東、浙江、廣西、北京、天津、江蘇等地也組織了醫療救護隊,馳援武漢。那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到底有多嚴重,未來會如何發展,目前如何防護,如何就診,最壞的情形是什麼,針對這些問題,金冬雁接受了《知識分子》專訪。
作為長期跟病毒打交道的人,病毒學家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熟悉病毒的那群人,病毒如何發生,如何傳染,疫情如何發展,如何防護,病毒學家都應該有話可說。在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金冬雁看來,武漢這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應對有諸多可商榷之處,他說,作為病毒學家,最重要的是和公眾坦誠交流。12月31日、1月3日、5日、11日,武漢市衛健委稱,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沒有醫務者感染;1月15日,武漢市衛健委稱, “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表示, “根據目前的資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傳人”;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宣布 “封城”。連日來,面對蜂擁而至的求醫者,醫療物資的短缺,促使武漢各大醫院紛紛發起了募捐活動,與此同時,軍隊醫院、上海、廣東、浙江、廣西、北京、天津、江蘇等地也組織了醫療救護隊,馳援武漢。那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到底有多嚴重,未來會如何發展,目前如何防護,如何就診,最壞的情形是什麼,針對這些問題,金冬雁接受了《知識分子》專訪。
《知識分子》:現在有一些研究,對病毒的源頭進行了猜測,你怎麼看?金冬雁:病毒溯源其實現在也不是最要緊的事。如果從進化上講,這些病毒最原始的源頭就是蝙蝠,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麼,蝙蝠怎麼傳到人的呢?比如說,人和蝙蝠中的MERS病毒(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非常像,也同時感染駱駝,駱駝是一個中間的儲存宿主,而且很多人相信,這個病毒在駱駝體內已經適應了,很多地方的很多駱駝都有,然後不斷傳播給人。因為中東地區駱駝很重要,不可能全部宰殺,所以從2014年到現在不斷有人類感染病例出現。也就是說MERS這個情況,中間有一個穩定的宿主。SARS病毒在果子狸等幾個野生動物都有發現,但情況不一樣。研究人員把MERS病毒種到駱駝身上,駱駝出現較輕症狀,已經過實驗研究。但沒有把SARS病毒接種到果子狸體內,觀察病毒的繁殖,怎樣傳給人等,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沒有解釋清楚。自然界野生或人工飼養的果子狸並未發現SARS病毒。現在武漢的病毒除了華南海鮮市場是確定的源頭,其他的市場也有問題。比如在白沙洲市場當會計的一位香港居民也受到感染,說明不同的野生動物市場肯定都是高危場所。但到底從什麼動物又如何傳給人,是不是通過哪個中間宿主,現在已經不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肯定是要果斷切斷、禁止野生動物飼養買賣,甚至連飼養都不行,因為不過正不能矯枉。全面查禁野生動物飼養買賣之後,要查出哪種動物受到感染更不容易,這個迷不容易揭開。如果此動物只是短暫或一過性的中間宿主,就像SARS病毒感染果子狸的情況,那麼也許永遠也無法重現華南海鮮市場或其他野生動物市場曾經出現的實際情況。新型冠狀病毒最大可能是通過某種作為中間宿主的哺乳動物傳給人。雖然此病毒的動物溯源作為重要的科學問題仍值得研究,但是目前動物顯然已經不再是傳染源,因此討論動物溯源對於防疫也是緩不濟急。金冬雁:蝙蝠可能直接將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傳給人類,之前非洲的大流行可能是由小孩在藏有蝙蝠的樹洞中接觸到動物或其唾液或糞便而開始。果蝠是此病毒的主要儲存宿主,人類通過接觸森林中受到污染的水果也可能受到感染。1998至1999年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暴發流行的尼帕病毒,也來源於蝙蝠,並可由蝙蝠直接傳染給人。蝙蝠有一個特別的免疫系統,使它成為很多病毒的儲存宿主,包括流感、SARS、MERS、埃博拉等。在美國出現的狂犬病毒感染都是蝙蝠造成的。蝙蝠會不會直接將新型冠狀病毒傳給人,並不能排除。因為吃蝙蝠而在宰殺過程中直接將病毒傳給人也是可能的。武漢病毒所石正麗教授已發現蝙蝠中有新型冠狀病毒的近親,病毒有可能從蝙蝠傳到中間宿主再傳到人,也不能完全排除直接傳播。但是現在的疫情裡面,已不再是由蝙蝠直接或間接傳給人,現在絕對是人傳人,最主要是要解決人傳人的問題。金冬雁:我還是有保留的,不能完全說沒有。現在需要把詳細的病人的資料公布出來,這對控制疫情和公眾教育都是有幫助的。一個病人如果把十幾個醫護人員都感染了,一個可能是因為醫護人員因不知道而沒有做適當防護措施導致受感染,另一個可能是病人病毒量特別高,或者是兩個因素同時起作用。如果說這個病人病毒量特別高,能傳這麼多人,他本身就是超級傳播者。是不是這種情況,需要做流行病調查的人清楚分析具體資料才能得出合理結論。其實從流行病學來講,很多調查工作都沒跟上或沒公開,沒有把情況查清楚,就已經翻篇了。做防疫工作的學者,應該大愛無私,儘快公開或發表對防疫工作有重要意義的數據,不能藏着掖着光想着發表大論文。金冬雁:病毒第一步由動物傳到人,然後這些人傳給第2代的人,肯定這兩個都發生了,而且由這些人傳給下一代的人非常有效,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是能人傳人,而且非常有效。但是從這些人傳到第3第4代的時候,是不是仍然這麼有效,還是減弱了,這一點目前仍無明確答案,有待觀察和研究,對於疫情的進展這是很重要一點。現在大部分的病例還是跟武漢有或多或少、直接間接聯繫,基本上還可以連到武漢,如果將來比方廣州很多都是從來沒去過武漢的人都受到感染(現在這部分人有,但是很少),就說明下一步的傳播也同樣有效。從SARS和MERS來說,再傳出去,傳播力都是減弱的,不會一直同樣有效地傳到4代、5代。如果再傳下去,它都不減弱了,就是說它已經完全適應人體。金冬雁:現有的人類冠狀病毒有4種是常見的,分別稱為229E、OC43、HKU1和NL63。其中HKU1和NL63是在SARS以後大家在跟進研究裡面發現的。這4種病毒引起的是普通感冒,比流感還要弱。這些病毒如果溯源,NL63和229E也來自蝙蝠,而OC43和HKU1則可能來自鼠類,但現在這4種病毒在人里已經非常普遍了,但只引起普通感冒。但是如果追溯回去幾十年,一兩百年或者更長時間,這些病毒剛剛進入人體的時候,也是一樣,會引起全球性大流行,有可能跟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或者SARS的情況相類似,但它最終的結果是什麼?是所有這些病毒最後都減弱成只能引起普通感冒,這是一個底。如果它確實是傳播力非常強,而且非常持續的話,我們做很多事情也逆轉不了的,那變成常規化管理就行了,我們不會因為一個季節性流感就把城封了,將來的最壞的一種結局就是這樣。歷史上的冠狀病毒都是減弱的,其他的大部分人類的病毒病原也是減弱的。病毒傳播得越好的時候就減弱了,因為如果它把人都殺光了,對病毒自己也沒有好處。金冬雁:現在看到,這個病毒是在肺裡面複製的,在上呼吸道並不能有效複製的,現在還沒有到普通感冒傳播性這麼高。肺裡面咳出來的痰,比打噴嚏的傳播可能要更有效,含的病毒量更大。所以,這個病並不像普通感冒、流感、天花、肺結核那麼能傳播。如果真是這麼強的傳播,我們擋不住,最多就是拖慢或者延遲。《知識分子》:從感染到有症狀,到底是多少天,14天?金冬雁:如果從香港大學團隊研究的一個聚集感染的家庭來看,也就2到6天,並不是很長。總體來說,兩周以後能傳的可能性就小了。當然這也是需要研究的,有沒有人病好了以後還傳播病毒的。金冬雁:很多的冠狀病毒,包括SARS,有人覺得在糞便也可能會有。新型冠狀病毒到底有沒有,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但是起碼現在沒有很明確的證據說糞便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主要還是飛沫。《知識分子》:懷疑接觸了但沒有症狀或者輕微症狀,在家隔離兩周,是不是就可以基本確定,不用擔心傳染給別人?金冬雁:對。對中症、輕症的患者,不能都擁到大醫院。造成恐慌的原因就是覺得這個事情不得了了。從武漢來香港的呈報的451例裡面,現在只有8例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其他的都是流感以及其他常見的呼吸道病毒。現在武漢同時處於流感高峰期,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實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是流感。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也是輕症、中症居多。如果所有流感病人及輕症患者現在都占用寶貴的醫療資源跑到大醫院,人群一聚集情況可能更糟糕。現在特別是輕症的患者,我贊成要居家隔離,通過比如網上的專家會診,給他們醫學甚至是心理的諮詢,給他們安慰,傳染病和臨床病毒學的專家應該告訴大家怎麼隔離,給他們建議,甚至有一些可以給他們開藥送藥,可以大大減輕中心醫院的壓力。金冬雁:據我了解核酸診斷已成瓶頸,都做不過來。診斷方面比如說結合胸部X光,用有效的辦法找出那些真正的中症、重症、高危的病人,集中起來去救治,把稀缺的醫療資源留給他們。對病人進行分級分流,這一點其實講深了,我們醫改也應該是走這個方向的,不能把中心醫院這麼拖死了。《知識分子》:國外發達國家的分診體系確實不同,但我們中國老百姓似乎習慣了直接找專家,動不動掛急診,尤其是恐慌的時候?金冬雁:我們國內就醫的心態和模式與海外相比很不一樣,第一找熟人,第二找最好的醫院,誰都找最好的醫院就把最好的醫院拖死了。這個是我們醫療制度深層的問題,那現在怎麼辦?現在我們也還是要病人分流、居家隔離,然後醫護人員給他們支持,別大部分輕症的把重症的拖死了。《知識分子》:最近有一項研究,早期確診的41名病人,有13名進了ICU,6人死亡,你怎麼看?金冬雁: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病死率(case fatality),就是說確診這個病的人數做分母,死的人數做分子。另外一個是死亡率,叫 mortality,分母是所有的易感人群總數,分子是易感人群中得病死亡人數。確診41名,6人死亡,15%這是病死率,是高的。我們推測,這個研究的研究者沒把輕症和無症的患者找出來。當然,要計算死亡率,其實要到最後都死完了,大部分人恢復了以後,那時候會算的比較準確。死亡率從現在來看,肯定沒有SARS高。金冬雁:現在的情況是漏診多過誤診。一般來講,第1次查是陽性,第2次是陰性的情況是很少的。但是有沒有可能漏掉?取樣取的不好就漏掉了,因為那個痰在比較深的位置。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檢測核酸了。但現在好像武漢那邊檢測不過來,很多輕症患者的心理也是我不就醫了,所以肯定是低估的。金冬雁:輕症在家隔離以後就好了,這是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有部分可能會轉化,所以要有醫生稍微指導一下,如果突然惡化的時候,再撈回來去救治,就是雙保險。金冬雁:其實這個病毒的疫苗並不是難做的,但疫苗也是緩不濟急,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出來。現在病毒還沒長得很好,你要把它做成疫苗,就要想別的辦法,但也不是沒辦法,也有很多辦法可能都是有效的,問題是等你疫苗做出來,可能疫情都已經結束了。藥是能趕上一些的,過去SARS或者MERS試過的藥、恢復期病人的抗體、一些有明確抗病毒活性的藥如干擾素等,是可以試用的。只能是特事特辦,國家可能快一些批,有一些試驗的東西做起來,但是這個也不是最急迫的,因為大部分人還是會自己好的,仍是支持性治療為主。《知識分子》:你怎麼看武漢封城這件事,是不是有些極端?金冬雁:這很複雜,是歷史上沒有採取過的。現在也不是來挑戰到底正確不正確,我們現在希望封城能收到封城的效果,也解決好各種次生的問題,比如民眾的心理問題,包括恐慌、逆反出逃,有的一早就走了,有的到外地隱匿身份等等。《知識分子》:現在看到一些醫院在募捐醫療物資,比如防護服、N95口罩,感覺物資不是很充足?金冬雁:其實一般來說,正確佩戴外科口罩就可以了,並不是所有人都要N95口罩。N95口罩應留給有可能長時間暴露於較大量病毒的人。我們國家大量生產外科口罩應該不是問題。民眾因為恐慌都是儘量採取最高級別的防護,去搶N95,但又不正確使用,把人家醫護人員用的防護衣都想拿來穿,這些都不需要。從公共衛生、臨床病毒學的角度來講,要教導醫護人員和民眾正確使用這些口罩。我們病毒學家,天天都在跟不同的病毒打交道,我們誰會因為研究這個病毒就受到感染?除非是新的病毒,我們完全都不知道它怎麼傳染,才會發生意外。新型冠狀病毒是通過飛沫傳播的,也是只有一定的條件下它才能有效傳播,不能草木皆兵。比如說吃飯會不會傳播?這種可能性還是很小的,不會的。最主要還是要跟大家講正確使用防護用具的辦法,不是說你使用了護具,你就萬能。人的警覺性和遵守一般規則的意識同樣重要。SARS的時候,北京P3實驗室、新加坡、台灣也出了病毒泄漏事故。也就是在最強的號稱固若金湯的防護條件下,由於人的疏忽大意而受到感染。這些慘痛教訓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知識分子》:那如何做好防護和醫療資源的平衡,看來臨床病毒學和傳染病學專家的意見很重要,這個目前是不是挺缺乏的?金冬雁:像英式體系,比如香港醫院的感染控制主任,權力大到院長之下什麼事都管,而且他會給前線醫師提供最確切的信息和辦法。中國傳染科是小科,大家都不想去,這是個深層次問題了。從SARS以後稍微重視一些,但基本上仍然比較弱勢。大家都想去那些高大上的科,感染科在整個醫院裡面的地位較低。金冬雁:一般的比如說中醫科、腦外科,只要沒有亂跑過來的受感染病人,接觸大量病毒的可能性較小,不需要N95。美國有研究認為醫師戴外科口罩和N95口罩預防流感的效果並無分別。《知識分子》:病人有其他併發症跑過來,是不是也會傳染?
金冬雁:這個是最麻煩的。像香港SARS期間有老人家受感染後又摔跤斷了骨,結果跑到骨科,把骨科醫生傳染上。這種情況是有的,但是現在大家都已非常警覺,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大大減小。提高警覺性是好的,但不能夠驚慌失措。《知識分子》:還有什麼問題是我沒提到而你想補充的?
金冬雁:如果從科研上講,研究其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像過去2003年SARS的時候,每個人都來做SARS,以後就都沒有人做了。中國科研人員的趕時髦,而不注重長期積累和深入研究的風氣,需要改變。這麼久以後,這次疫情再來了以後,很大程度上又重犯了2003年的錯誤,從臨床病毒學、心態上、技術上、處理上都有問題,這一點其實是很痛心的。當務之急,要處理好封城以內的人的情緒,正確引導他們對於這個疾病、對於病毒的認識,而且要把最壞的情況交個底兒說清楚了。其實,最壞也沒到壞到什麼程度,也不會比季節性流感更壞。季節性流感死的人更多,毒性、傳播力更大,而且造成的損失也更大。
金冬雁,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一位經驗豐富的病毒學家,對病毒性疾病和腫瘤學有濃厚的研究興趣。他試圖了解為什麼病毒會導致不同的疾病,以及不同的DNA和RNA病毒如何入侵宿主的先天免疫力,這些免疫力是人類抵禦這些入侵病毒的第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