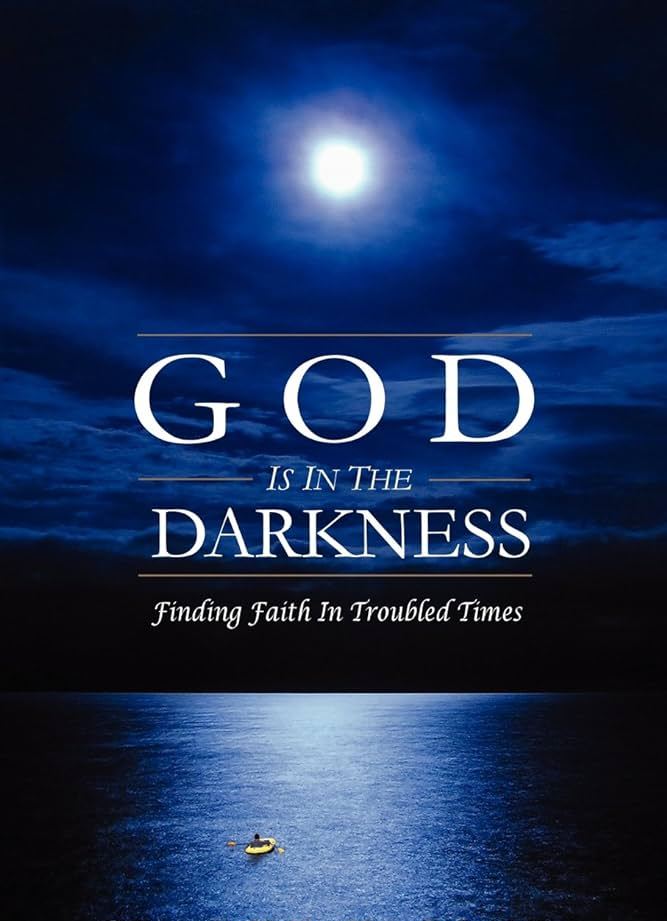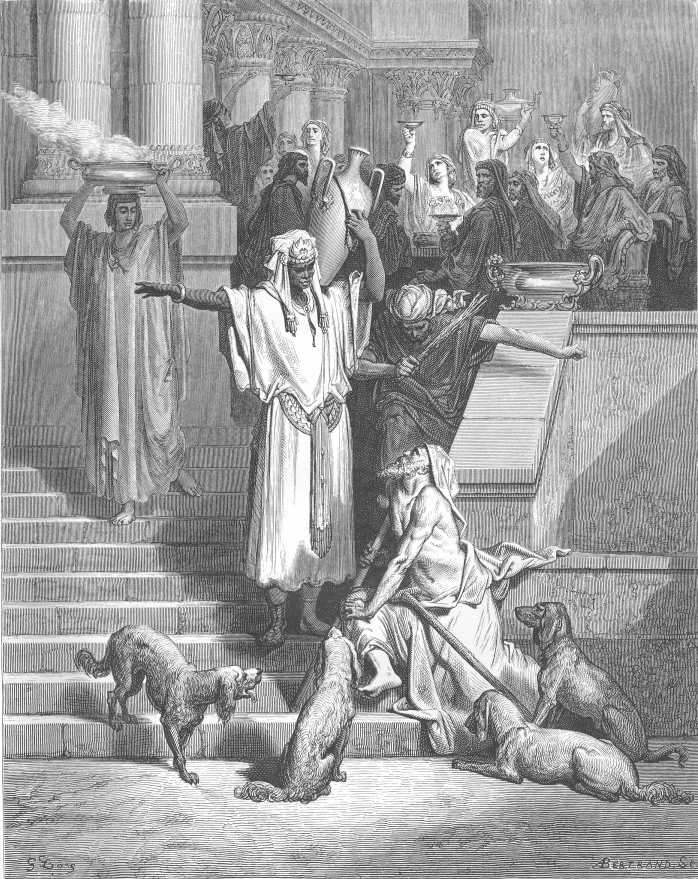| “拉撒路”奶奶 |
| 送交者: 生命季刊 2023年09月27日01:53:48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
“拉撒路”奶奶
文/安朴 《生命季刊》總第2期 1997年6月
音頻為以琳姊妹朗讀:
三一神學院的學習頗不容易。那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Dr. Ward屢屢聲稱,他要培養“科學的”基督教教育家,作家,研究家,所以寫文章要客觀,絕不允許第一人稱出現,以杜絕主觀色彩;只有無主觀,文章才顯得客觀、冷峻,才顯示其“科學性”和“理性化”。一次,為了鍛練這些未來的基督教教育家的科研能力,他要求每一個學生選擇一個與自己未來服事領域有關的題目,利用 CD ROM 和 ONLINE 等世界最先進的電子科研設備,調資料研究自己的題目。當然文中是不允有“我”字出現的。
我選擇了一個“信仰與苦難”(Faith and suffering) 的題目,擬從神學、哲學、心理學三個領域探討信仰與苦難的關係。然而,我天生不是一個“科學的”研究者,面對着電腦屏幕輸入“suffering”這一提示詞 (indicator) 時,面對着堆積如山的夾有德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的英文資料時,我常常心猿意馬,走神兒都不知走到哪裡去了。
記得那是一個陰雲密布的清晨,幼年的我在姑姑家住了一段後,又輾轉回到自己的家。初春的凌晨,整個小鎮死一般的靜寂、冰冷;窄窄的長街闃無一人,沿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竟有一半是衝着父親的。黑色的大刷子刷出的父親的名字倒寫在巨大的白紙上,並打上了腥紅的叉。雖然我已經習慣了父母親屢受逼迫的現實,但我還是又一次感到恐懼,那幼小的心靈還是又一次感到了承受不了的沉重。天更加暗了,遠處傳來一陣雷聲,風簌簌吹了起來。窄窄的長街的盡頭,似乎有一位撿破爛老人影影綽綽的身影;此外,小鎮再無一絲生氣……
父親已經被打傷,躺在家中;這次他右側的肋骨被打斷了。父母親都不是本地人,但已在此地落根經年;由於父親極高的醫術和極好的見證,他在當地人中享有極高的聲譽。父親被打傷後,那些不吃皇糧、因此也不識政治時務的市民、農民們便絡繹不絕地前來探望他。醫院的造反派只好在我家的大門口外擺了一張長方形的課桌堵住路,兩個帶有“紅醫公社”大紅袖章的人值班站崗,凡有人走近,便喝道:什麼成份?來做什麼?然後宣講父親是“反革命份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務”,勸其劃清界線。大多數人都會慌亂地囁嚅着離開。然而,也有個別性情剛烈的壯年漢子吼叫:“老子是僱農!你能把老子怎麼着!”
下午,大門輕輕地被推開,一位挎着籃子的老太太閃了進來。她外形極其平凡,一件深藍色的大襟褂子補滿了補丁,背微駝着,蹣跚走進這個已被嚴嚴監視的家。( 不知她是怎麼進來的?) 她問候了父親的身體,安慰他說:“先生,你要挺得住,要想開些……”父親連聲答到:是的,是的。而後,老人回頭看了看我,略有遲疑,然而還是轉過頭去,低沉卻又清晰地對父親說:“先生,記得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嗎? 祂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這些經文不是預表耶穌嗎?”
父親立時無比欣喜地、低沉而又堅定地回答:“是的,是在講耶穌。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那位老人接着用更低沉的聲音安慰父親說:“先生,耶穌與我們同在……我們禱告、仰望祂吧!”
老人的來訪時間並不長。她匆匆離去後,我問父親:“她是誰?”父親回答說:“她是我們城中的拉撒路啊!”
“拉撒路是什麼?”我不解地問。 “拉撒路是聖經中的一個人物。他是一個乞丐,渾身生瘡,在世上受苦,但死後就進了天國……”
我想起了早上的情形。是她,一位撿破爛的老人,烏雲密布的時候,雷聲響起的時候,是她挺直了身子,屹立在長街的盡頭……
那天午夜後父親在暗中的低聲禱告中,又一次充滿了對主的嚮往與感恩。他深信主耶穌基督在我們的苦難中與我們同在,他特別感謝主耶穌賜給他“美好的主內團契”。那時,我並不懂“主內團契”是什麼意思。
北美A城華人教會社青團契通知:團契活動訂於本周六下午五時於中國城富麗華酒家聚餐,請弟兄姊妹務必出席,共享愛筵。
Walter A Elwell主編的《福音神學詞典》(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中,對“團契”(Fellowship) 一詞的解釋為:此詞源出希臘文 koinonia,英文解釋為“participation”,中文應理解做“參與”,或“共同經歷”,其中包括“分享”與“分擔”。聖經中的“團契”(fellowship),是指真正的信徒與基督共同經歷苦難( 腓立比書 3:10 ,彼得後書 4:3);與使徒們一同經歷苦難( 哥林多後書 1:7) ;與自己的同胞一同經歷苦難( 希伯來書 10 : 33)。
德國神學家、殉道者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1945) 認為,基督的一生總括為兩個字:苦難;而教會是做為團體存在的“基督”,教會是應該與基督一起經歷苦難的。
此後零零星星從父母口中聽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孤寡老人,鎮上的“五保戶”。她生平坎坷,地位卑微,卑微得連個名字都沒有,卑微得沒有人意識到她的存在;人們偶爾提到她時,只是稱她為“新街的老婆子”。然而,就是她,在瘋狂和恐怖交織的歲月里,她冷靜地、無畏地甚至是頑固地表達着自己的信仰。當江青不無驕傲地向外國記者宣布“中國已經沒有宗教了”的時候,她卻在山呼萬歲的喧囂聲中,微弱但執着地對人傳講“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的消息;城中另一位五保戶董奶奶,就是在“中國沒有宗教”的時候,聽到了她傳講的福音;董奶奶重生得救後安然去世。
記得後來,也許是我已經長大成人,我開始參與一點兒“父親的事情”。記得那是人們開始準備“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的臘月,父親囑我去給她送一些過年的食物。她住在一個大雜院裡的東南角的一間破房子裡,確切地說,是一間不堪風雨的窩棚,歪歪斜斜的屋頂,歪歪斜斜的窗。令人奇怪的是,大臘月天,她的門口卻吊着一掛竹簾。我喊了一聲“奶奶”,掀帘子進去,便明白這竹簾後的奧秘了:她正在以一個無比粗笨的木凳當桌子,坐在一個矮凳上,借着門口的自然光,捧讀一本黑色封皮的《新舊約全書》;若關了門,整個房間就是漆黑一團,掛上竹簾,為的是既能讓光進來,又防止外面的人看見。房間內,可以想像會有多麼簡陋,唯一的桌上放着一盞最原始的煤油燈。已經是七十年代了,電燈線卻掠過她的屋頂,伸向別的人家,她還需要用煤油燈照明。
她驚喜地說“妮兒來了”,便慌忙為我找座位,又慌忙用家裡唯一的一隻碗給我倒水喝。我坐下來和她聊了起來。我當時不知道應該問她的“見證”,我問了許多問題,大多是關於她的身世的。
她於 1900 年出生,四歲便成了孤兒,在山東滕縣宣教士辦的孤兒院中長大。成人後,孤兒院做主嫁人。婚後無子女,她的丈夫“1958 年時,餓死了”,她用極平靜的語調說,“他飯量大,吃不飽,後來就餓死了。死後,買不起棺材,一領席捲了,埋了。”她述說的時候,滿臉的平靜、祥和;我驚訝她的敘述,仿佛她丈夫的死,只是因為“飯量大”所致;她沒有一絲抱怨,甚至沒有一絲悲嘆。
在這個世界上,她一無所有,無親人,無財產,年紀大了,又喪失了勞動能力,街道每月給她五元錢的五保戶生活費;此外,她也每日出去撿一點兒碎紙片兒之類的破爛,以賣幾分錢維持生活。我至今不知她叫什麼名字,我喊她“奶奶”,在我的心裡,她永遠是“拉撒路奶奶”。她也從沒有問過我的名字,她按當地人的習慣,稱我為“妮兒”,如有我的姊妹在場時,就稱我“二妮兒”,以與我的姊妹“大妮”和“小妮”區別。
她在孤兒院裡學聖經,中文識字,及編織針線等女工。她說她認字不多,只認聖經中的字。我看到她的聖經旁邊有兩片縐巴巴的紙片,顯然是小學生“田字練習本”中尚未用完的最後一兩頁,她撕下來自己用了。我看到紙片上恭恭正正寫滿了字,每一個字都頂滿了格:“我信我信耶穌基督是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神的兒子我信耶穌為救世人被釘十字架三天復活升天我信人都有罪唯信靠耶穌罪得赦免……”我看着這滿紙諸多的“我信我信”的字樣,不禁又抬起頭來看她,她那平靜的面容中,又透出幾分老人家特有的安詳和堅定。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在她這裡聽不到“平生遭際實堪傷”的悲嘆,看不到“天涯淪落、身世浮萍”的痕跡。
當代神學家麥克羅斯 (Alister McGrath) 綜述馬丁·路德關於信心與經驗的觀點時指出,神看起來似乎缺席,但實際上卻有祂隱藏的同在。信心乃是看見神在這個世界上及我們本身經驗中同在、動工的能力。信心就是當經驗暗示着神缺席時,依舊願意相信神所應許的,敞開心期待神的作為。路德用“信心的幽暗”(the darkness of faith) 一語來闡述他的看法。這項看法幫助他明了懷疑的本質。懷疑表現出我們習於靠經驗判斷事物而不靠信心的天性。當信心與經驗相持不下時,我們傾向於信賴經驗,而不信賴信心。
後來的年月中,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我每次回到父親的城,總要去探望她,而幾乎每次見到她,她都是在讀經。我就是這樣走進了她的“查經班”。我漸漸明白,她信心的源泉就來自這本偉大的奇書聖經。聖經對她來說,是一本指導、參與她的生活的書,一本關於人類命運的偉大預言書。對她來說,文革中的瘋狂和騷亂,階級鬥爭導致的夫妻反目、父子為仇的現象,“備戰備荒”的偉大號召,唐山大地震、乃至計劃生育運動;中國人民、中國基督徒以及她自己所經歷的一系列的苦難,——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可驚奇的,這一切都是全能神的計劃中必然發生的歷史事件,而且早就記錄在聖經中了。她總是緩慢地、清晰地、一字一句地讀給我聽:“你們也要聽到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聖經在她的閱讀中,不再只是具有抽象的遙遠的意義,而是實實在在地干預和指導着我們周圍的生活。當政府以“先收地、後扒房,逼死人命不用償”的決心推行計劃生育時,她淡淡的一句話:“聖經上說,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便消解了許多人的困惑。連我至今也看不懂的啟示錄,在她的朗讀和理解中,也是清晰而又具象的。
我驚詫她的聖經知識的嫻熟,更驚詫她那先知般的睿智。鄧小平剛剛復出時,她就敏銳地提出,要為鄧小平禱告。我不解,為什麼她,我,我們這樣的小人物,為那個高高在上的執政者禱告,有用嗎?她又一次堅定地說:“為他禱告,求神軟化他的心,給全中國的人信主的自由!”
我相信有大信心、大智慧的人禱告一定更蒙神垂聽,所以一次我央她為我的信心禱告。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一次她卻不那麼“仁慈”。她說:“你應該自己禱告,神會垂聽你的禱告。”當時我似乎有些失望,但後來也就明白了她促我禱告的好意。後來她還是和我一起跪在她那高高的秫秸棚起來的草床上禱告。幽幽暗室中,她的禱告是那樣的真摯和自然。她感恩的話語,如溪水般涓涓流出,她不僅感謝神給她的救恩,給她的平安和喜樂,也感謝神給她的貧窮和卑賤;她對人的愛心,如春蠶蠟燭一般執着;人們藐視她,踐踏她,視她連路邊草芥都不如,而她則切切地為“全中國的人”禱告,切切地為執政者禱告,為全中國的人都能得救,都能享有那永恆的喜樂平安而禱告。誰敢說她的禱告不蒙垂聽呢?文革後宗教政策相對的放寬,八十年代後家庭教會如火如荼般的興起,不是神對她的禱告的應允嗎?
赫勒 (Friedrich Heiler) 總結出人類經驗中的六種祈禱類型,即:原始祈禱,儀式祈禱,希臘文化式祈禱,哲學祈禱,神秘祈禱,先知式祈禱。其中先知式祈禱為最高祈禱形式。先知式祈禱的基礎不僅是出於需要,更重要的是出於愛。先知式祈禱中沒有成套的術語,也沒有神秘的冥想,它是一種深沉愛心的自然流露 ( 渲泄 ),是出自內心的恆切祈求。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德國集中營工作的醫生目睹了潘霍華的殉道。他敘述道:“那天清晨,囚室的房門半開,我看見受人愛戴的潘霍華牧師在脫去囚服前,先跪在地板上熱切禱告。他的禱告使我極為感動:他禱告得是那樣的虔誠,那樣的專注,他確信神垂聽了他的禱告。到了刑場,他又一次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然後他走上了絞刑架的台階,勇敢堅定,從容自若。幾分鐘後他便被處死了。在我做醫生的近五十年的生涯中,我從沒有見過一個能夠這樣完全交託、完全順服神的旨意、從容就義的人。”
Dietrich Bonhoeffer (4 February 1906 – 9 April 1945)
“讓我們開始禱告吧!”牧師對着坐在空蕩蕩的教堂里的七、八個人說,“代禱的事項有:Mark 全家下周去旅遊,他請我們為他的旅途安全禱告;九月二十八號,教會有在 Central Park 烤肉聚會,請大家禱告,神給我們好天氣,不要下雨……”
時光倥傯。八四年夏天,我逃難一般回到了父親的城。那時我已經成家。嚴格的說,是結婚了沒有“成家”。我是傻乎乎地嫁給了一個同樣傻乎乎的有“政治問題”的丈夫,於是婚後無住房可言,也無家可成。到了該生孩子的時候,乾脆跑回娘家,和父母親、妹妹等一大家人擠着住下來。
那是盛夏時分,這次奶奶先來看我了。她織了一些花邊送給我,說是可以為孩子做衣服用。她似乎更老了,穿一件白色的大襟褂子,背比原來駝得更厲害了,滿頭灰白的頭髮幾乎變成純白了。只是她滿臉的慈祥依舊,笑咪咪的,慈眉善目中掩不住的喜樂。
“奶奶,有什麼喜事啊,這麼高興?”我問她。她高興地說:“有啊,我正要告訴你呢。前些天下暴雨時,我的房子塌了。半夜裡,我正睡覺,風颳得太猛了,雨下得太大了,一根屋梁從山牆上砸下來,正橫着棚到我身上。鄰居們起來了,把我從泥水中扒出來,我渾身上下好好的,連一根汗毛都沒傷着!這豈不是神的恩典嗎?感謝主!”
我想起了她那歪歪斜斜的小屋,倒塌也是在意料之中。房子倒塌,竟沒有傷着她,實在是神的保守。我關切地問她:“你現在住哪兒呢?”“哦,我現在住在教堂里了。”她還是不無喜悅地答道,仿佛能住進教堂是莫大的福份。“教堂里哪兒有地方可住呢?”我疑惑地問。她卻仍然喜孜孜地告訴我:“教堂里的樓梯底下,很好的住處呢!”我當時還替她慶幸,覺得她總算是有個棲身之處了。我自己不正在發愁孩子出生後沒有住處嗎?
然而,直到第二年的冬天,我才真的看到了她的“很好的住處”。那年一放寒假,我便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匆匆逃離了學校分給我的十二平方的陋室,回到父母家過年。一天中午,孩子睡着了,我突然想起,應該去教會看看奶奶了。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奶奶正坐在教會的院子裡,邊曬太陽,邊吃午飯。她的右邊放着一隻小小的用瓦盆和泥巴糊成的燒柴禾的鍋灶,手中端着一隻盛着麵糊糊的飯碗。她看見我非常高興,我見了她連忙問:“奶奶你吃飯了?”“奶奶你冷不冷?”她知道我並不會世俗的寒喧,她知道我是實實在在地關心她的溫飽冷暖。她便慈愛地告訴我她生活得很好,她說她不冷,她穿着深色的棉襖棉褲,她告訴我她棉衣里的棉花都還新着呢。她滿頭的銀髮在微風中輕輕地飄動,滿面的慈容在燦爛的陽光下更顯得慈祥。
然而當我說“奶奶我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去”時,她卻顯出慌亂的神情,她說:“妮兒,不用了,你不用去看了。”她竭力阻止我走進教堂。我不聽她的勸阻,轉身走進教堂。
其實這個教堂是我從小就非常熟悉的地方。兒時的記憶中它壯麗而又輝煌。環繞教堂的十六個巨大的拱形窗戶上嵌的全是七彩玻璃。而今,那昔日的光彩蕩然無存,七彩的玻璃早已被打得粉碎,整個建築磚牆剝落,門窗俱損。推門進去,一股寒氣襲人。舊時的紅漆地板早已不翼而飛,濕冷的泥地上擺着一條條長凳。這個八面透風巨大無比的空間,主日時擠一擠,可容納一千八百人聚會。西北角的樓梯底下,約有兩平方大的梯形空間裡,陰濕的泥地上鋪着約有半尺厚的稻草和蓆子,蓆子底下墊了一塊磚做枕頭,蓆子上面是一床被子和兩床棉被。這便是奶奶的臥室了。整個大教堂里無任何取暖設備,那眾多巨大的門窗個個是千瘡百孔,難遮風雨。
我回到陽光照耀的院子裡,心中十分憂愁,對她說:“奶奶,你簡直是在露宿啊,天這麼冷,你住在這兒怎麼行呢?”奶奶抬起頭來,她仍然是無絲毫的憂怨。她只是為我的憂慮而不安,仿佛讓我為她擔心是她的錯一樣,她反而連聲安慰我說:“妮兒,我不冷,你沒有看見我有兩床被子嗎?不礙事的,我不冷……先生和許多別的人都照顧我呢!”她滿頭的銀髮在微風中輕輕地飄動;聖潔的面容在陽光照耀下熠熠閃光,那光芒輻射出來的,分明是仁慈,良善,和平,喜樂,感恩,謙卑,忍耐。
沒想到那次陽光下的會晤竟是最後一次在這個世界上見到她。
數年後我欲負笈美國的前夕,匆匆回來與故鄉告別。問及奶奶的情況時,父親告訴我,她已經安然去世。她是在教堂的樓梯底下睡過去的。儘管我知道她有永恆的生命,但我心中還是有一種說不出、說不清的難過和惆悵……
有一個財主,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舔他的瘡。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就喊着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里,極其痛苦。”
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達美國後的第一個主日,去郊外一間華人教會崇拜。我第一次踏進北美的教堂。腳下是鬆軟的地毯,頭上是明亮、柔和的燈光;四季 F 氏 70 度的恆溫;豪華,富麗,堂皇。到處是有用或無用的空間。我突然想起了她。如果奶奶能有這一塊空間棲身!一進門的那間供人穿過的門廳,恐怕能容納下十個奶奶那樣的人居住……
主日學已經開始了。一個弟兄正在分享他從黃石公園退修會歸來的收益。他說他聽了很多 workshop,學到了很多,從如何理財到夫妻相處。他說到一些“stock”,“mutual funds”這些我根本聽不懂的字眼,還有一些我聽了似懂非懂的句子,比如“夫妻之間仍然要 keep dating”等等。他講得很生動,很幽默,眾人不斷爆發出歡快的笑聲。而我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我站了起來,衝進了衛生間,任憑淚水傾泄了出來……
崇拜結束後,我和兒子手拉手走出教會。七歲的兒子若有所思,突然問:“媽媽,他在哪兒?”我不解地問:“什麼?你說誰?”孩子很認真地說:“我是說神。神在我外公的那個很多人很擠的教會呢,還是在這個教會呢?”停了停,他又接着問:“他是更愛我外公那兒的人呢,還是更愛這兒的人呢?”我竟無言以對。
牧師讓我在教會的差傳會上“做見證、分享中國的情況”。我的第一個感動就是我應該講奶奶的故事。誰知我在講述的時候才發現,或許是因為我語言無力、詞彙貧乏,我無法把她的苦難的一生中的美好見證講出來;也或許是因為我和聽眾之間的文化隔膜所致,我竟無法真的與聽眾在“主內交通”。聽講的三十多位會眾中,能真正聽懂“拉撒路”奶奶故事的只是少數。聽眾中有一位性格開朗、活潑樂觀的姊妹,我每講一句,她必發出笑聲。我說奶奶四歲成了孤兒,她大笑;我說後來她丈夫餓死了她成了寡婦,她笑;我說奶奶每月只有五元錢的生活費,她又大笑;我說奶奶後來住在教會的樓梯底下,她竟然又笑了一下。其實我很喜歡這位姊妹,說起來我們應該是老鄉,她是在台灣出生的,但她父親就是我們那個地區的人。我問她回過老家嗎?她告訴我她“從來沒有回去中國”,但是前兩年“我爸爸回去找到了他的大女兒,他的大女兒可慘了”。她很單純,她的性格也很好,我知道她笑絕無惡意,她笑只是因為她無法理解、無法想像什麼叫苦難,而這種無法理解使我內心感到深深的悲哀。
約翰·斯托特 (John Stott) 在“絞刑架上的上帝”一文中指出,聖經明確地表明,上帝不僅當年與基督一起受難,而今祂仍然與祂的人民一起經歷苦難。耶穌說“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這表明了祂與所有的貧困、苦難者的認同。在一個充滿苦難的世界上,人們怎麼可能敬拜一個不可能受苦的上帝呢?
我的關於“信仰與苦難”的科學研究最終結束了。我瀏覽了許多神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的着作,光是這些著作的概要便集了86頁。我發現在經驗範疇里,人們幾乎沒有什麼異義,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都確認和倡導信仰在苦難中的積極意義。而在理論領域,眾多的大家們則各抒己見。我粗略地總結了他們對苦難問題的十二個類型的答案後,仍然覺得不甘心,於是便錄了一段 Mckenzie 的話:關於苦難這個古老的話題,過去的兩千五百年來,並沒有新的進展;所有現代觀點都是過去文化遺產的翻版而已。然後我結論說:苦難是一個體驗性的、非理論性的問題,人們只能在信仰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做出理性的或理論的解釋。在信仰與苦難的衝突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別的,正是信心。
任何一個靠着耶穌基督的受難、流血被拯救出來的人,都應該能夠理解苦難。
後來我再沒有對人講奶奶的故事。
然而我常常想到她。每當我走進教堂、會議室、圖書館等建築物時,或者什麼人的五室三廳的大房子時,那寬敞、舒適、設有沙發茶几的門廊或過廳總讓我想到奶奶樓梯底下稻草鋪起來的地鋪。我也常在默想中思索她生命的意義,她那陽光照耀下的聖潔面容也一再在我腦海中重現。她一生恪守信仰,仁慈良善,謙卑忍耐,無怨無悔,安貧樂道。若不是她對神的完全的信靠,對神的全心的嚮往,她怎麼可能做到在恐怖中臨危不懼、在貧賤中充滿喜樂、暴風雨的泥水壓下來時發出讚美、寒氣逼人的耿耿長夜中處之安然呢?我知道神通過她教給我信心的功課,我感謝神厚愛我,賜我這樣的福份,能夠結識老人家這信心的典範。然而,與此同時,我每每感到一種深深的內疚在譴責着我的心。那次在陽光下的教堂院中見到她後,我沒有再去看望她。或許我的理由很充足,我的孩子太小,我需要照顧他;我很少回父親的城,我沒有機會服事她。然而我知道這一切都不是理由。實實在在的理由是那時我愛自己——自己的兒子——勝過愛我的鄰居。我很後悔。雖然當時大家都很苦,雖然我無法替她找到一間棲身的小屋,但至少我應該多去看望她,至少,我應該端一盆溫熱的水替她洗熱那凍僵的腳,讓她能睡暖一些……
每當這時,我便聽到那來自上方的無聲的聲音:“你還有機會。你的祖國還有千千萬萬個拉撒路,他們在餓着,渴着,他們作客旅,他們赤身露體,他們生病,他們在監里……去吧,服事他們,做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聽到這聲音,便匍匐在地,掩面戰兢,說:“主啊,主!我聽你的吩咐,我要去。我在這裡,我願意!”
安 朴來自大陸,現為傳道人。
----------------------------------------------------------------------------------------------------------- |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復熱帖 |
|
|
|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22: | 在彼拉多面前的主耶穌 | |
| 2022: | 早晨 | |
| 2021: | 福音派教會裡的“社會公義福音”(含音 | |
| 2021: | 【里程信仰問答之七】相信耶穌基督是拜 | |
| 2020: | 神有主權,但神也看人行事。 | |
| 2020: | 轉:華人牧者關於2020年美國大選之勸勉 | |
| 2019: | 也談四種愛(zt海外校園) | |
| 2019: | 亞伯拉罕獻以撒(zt生命季刊) | |
| 2018: | 奇妙的“不料” | |
| 2018: | 大法官的聽證會蠻有意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