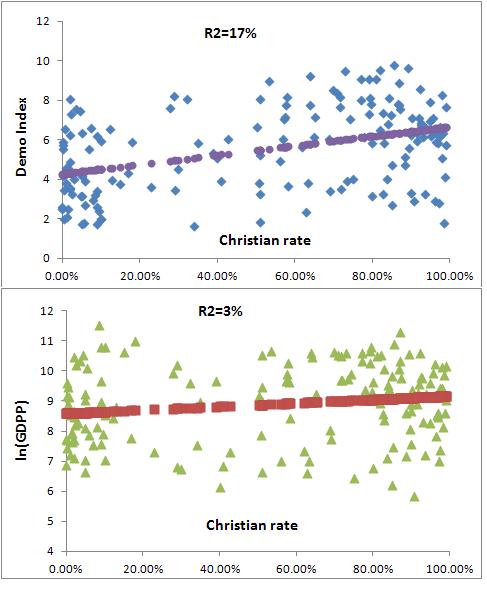| “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注1)”,这是研究初期教会历史及近代中国教会历史的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名句,并应用于基督信仰的宣教。W.Lee Troup说:“受苦永不是受欢迎的,但它却常与神国的增长连在一起。十二使徒中只有一位是例外,其余的都是殉道而死;现今(1989)估计每年约有35万人因其信仰而牺牲,殉道士的血时教会的种子仍然是真理。(注2)”于现今的世代,殉道事件并未因人类科技和文明的进步而减少。据估计,如今每年殉道数字大约在16万至20万之间。受苦与教会增长,在中国近代教会发展总是一个主题;因为对中国的信徒来说,受苦从来不是一个哲学的命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场景。 中国于81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前宣教士如Thompson Brown,David Adeney 等人都故地重游,但他们都惊讶地发现,由50年代海外宣教士全数离开后的中国大陆,历经多次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却是生命力强盛,其增长叫西方教会增长学学者为之震动。1949年中国大陆信徒大约在80万左右,但改革开放之后,单以所谓三自教会的数据,当时大约在1500万左右,然而到了现今2010年,则大约增长到了2000万左右了,这还未算上无法有客观数据记录的所谓家庭教会。据保守的估计,其数字大约也在7000多万,比较宽松的说法则可能有1亿3千万之多(注3)。学者们虽然对数字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们都同意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讶的。 20世纪世界教会历史的研究,中国教会的发展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如欲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二个表面上看似无法并存的现象,那就是受苦与增长。许多学者与宣教士都共同发现“受苦与增长”这二个现像并存于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中,赵天恩博士甚至认为中国教会的增长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受苦。10多年前,曾有一个关于普世教会发展的研讨会,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分享中国教会的发展,其理论也如赵博士的论点。 可是,在这个研讨会当中,有一位日籍的教授当即发问:“首先,假如受苦是教会增长的原因,那么中世纪北非的教会历经回教势力的入侵;然而,其经历的受苦却是叫北非教会差不多全然被毁,影响至今,不得恢复。其次,日本于二战以后,因着核武器的遗害,让社会民生遭了苦难,可是这却让今日之日本成了福音的一片硬土。请问:所谓受苦能导致教会增长的理论是否准确呢?” 所以,假如单纯地认为受苦是因,增长是果,并不能完全回答二者之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从信徒的生命来看,二者之间必须以顺服作为连结;没有信徒的顺服,受苦有时只能带来教会的毁灭,而非增长。可以这么说,中国近代教会的增长是因着信徒的顺服,而苦难是信徒顺服的场景;故此,中国近代教会的历史是一篇顺服的历史,而并非一篇单纯受苦的历史。 ......
注1:此名句出自土特良(Tertullianus)的《卫道篇(Apologeticum)》,原文“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seed”应直接翻译为“基督徒的血是种子”。 注2:W.Lee Troup,“Discipleship:An Invitation to Suffering”,Ambassadors Communique 26:1,6。 注3:对于中国大陆的信徒数字的确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这全在乎不同学者的立场和观察。但是,无可否认,其信徒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 注4:Chao,Jonathan,“Toward an Evengelical Theology in Totalitarian Cult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cialist China”,In the Bible and Theilogy in Asian Contexts,Bong Rin Ro and Ruth Eshenaur,eds. pp.342-264,Taiwan: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19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些文字来自于华神马志新老师的论文《中国近代教会研究的焦点》。本人认同马志新的思考。若由此而起的一切争议,责任全在于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