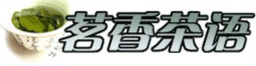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七壇甘草梅--2 |
| 送交者: 葉夢 2006年01月11日08:59:48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七壇甘草梅――周揚與吳淑媛(四) 葉夢
1934年深秋,吳淑媛懷了三兒子約瑟。周揚送她帶着兩個孩子回益陽分娩。往常,周揚總要等到嬰兒落地他才返滬。但這次沒有,他沒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他告訴吳淑媛,若是男孩子取名約瑟,若是女孩子取名亞密。周揚臨走時,他給吳淑媛留下一本淺綠色的信箋紙,那上面印了一隻飛翔的鴻雁。周揚對淑媛說:“你要常給我寫信哦!”身懷六甲的吳淑媛,接下了那本信箋,她萬萬沒有想到她愛的運宜會生二心,她沒想到,她和他之間以後只能是信箋上來往的夫妻了。她當時更沒想到,此行一別,和丈夫竟成永訣。 她原想夫妻別離時間不會長,生了孩子過一段即去上海。上海有他們租的房子有他們的家。大兒子已在小海念小學了。她與周揚夫妻12年,在上海呆了9年。她已經習慣了上海。然而天真的吳淑媛沒有想到,她永遠也回不了上海那個家了。 據陳子展先生對周艾若回憶說:1934年深秋周揚一家離滬的次日,他去周家,才知一家人己走,但門上掛了一件紅色的女大衣,他說:那大衣不是你媽媽的,你媽個子高,那紅大衣是小個子女人穿的。 據梅志先生回憶,周揚在1934年從益陽再度返滬,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已經煥然一新,他已換下慣常穿的西裝,着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有了另一個女人。人們再到周揚家,再也看不到那兩個在矮桌上玩積木的漂亮的小男孩以及那個身穿旗袍的賢惠的周夫人了。 上海灘上周揚的新氣象,遠在幾千里之外益陽城裡坐月子的吳淑媛一點也不知道,她順利地產下又一個漂亮的男孩子,她還沉浸在又一次做母親的喜悅與忙亂之中。 三兒子滿月之後,吳淑媛開始用周揚給他留下的信紙寫信,淺綠色的信紙一頁一頁地寄出去了,然而信發出了卻久久不見回信,再連去幾封也依然杳無音訊。當她終於收到周揚的信時,周揚在信尾這樣問她:你怎麼老不給我來信呢?吳淑媛接到丈夫的信後笑咪咪地對兒子們說:“你看你爹爹,我給他寫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還說我老不寫信。”現在看來,吳淑媛給周揚的信,也許真的沒有到達周揚手中。 轉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兒子一天天長大,又白又胖。按理說,吳淑媛又該啟程返滬了。這時,周揚來信,信上說,我暑假回益陽。於是吳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買了最好的梅子,周揚喜歡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開始為周揚做分別後的第一壇甘草梅子。 吳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別好。梅子做好了,孩子們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給爹爹做的。曬好的甘草梅子用一隻粉彩瓷壇裝着,放在雕花的紅漆擺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來了,周揚卻不見回來,那一瓷壇甘草梅子沒有人動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吳淑媛又開始為周揚做第二壇甘草梅子。這時,周揚又來信了,說今年暑假回來,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吳淑媛根本不會想到其中變故,倒是吳公館一位老傭人力勸嬌小姐攜子返滬,吳淑媛則說:“他不來接我,我是不會去的。” 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揚又沒有回來,也在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揚仍保持與吳淑媛的聯繫,還給兒子捎過一件紫紅色的呢大衣。可能是托人從外地買的。到1938年,吳淑媛還收到周揚寄來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吳淑媛讀着丈夫的譯著,一邊動手為她做第四壇甘草梅子。 周揚的母親這時寫信責問兒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的人都忘了?周母最耽心周揚發生婚變,她喜歡這位老實的不愛說話的二兒媳,怕她受委屈。周揚立即給母親覆信。信的大意是:我現在在膚施(延安)當教育廳長,我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還有一個最怕周揚變心的是吳周氏、吳淑媛的媽媽。吳周氏身染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但她不放心。她愛女兒勝過愛自己。她還愛女婿和3個漂亮的小外孫。如果可能,她情願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女兒的幸福。然而女婿數年不歸,這意味着什麼?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訴女兒。為了女兒一家,她曾經把家裡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給女兒。然而,她盡她所能為女兒所做的一切,並不能使女兒獲得幸福。 吳母的病逝使這位從小在母親卵翼下的女兒突然感覺天塌了。她只覺得眼前一片黑。 吳母埋在羞山附近。在母親亡故的那些日子裡,吳淑媛天天領着3個兒子和養女亞密一行5人,早飯後步行去數里之外的墳地。本來並不愛哭的吳淑媛把一世的眼淚都給了她母親,她哭娘,哭得天昏地暗,地動山搖。她開始是哭訴,哭的內容一天一天從不重複,然後是哭嚎,引得兒女們跟着她哭成一團,哭聲驚動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攏來,扶了她回羞山長田坊的莊屋。她哭娘的墳,先是每天一次,繼而隔天一次,連續哭了數月。 世間的榮枯難料,沒想到闊氣的吳家也會敗落,吳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投資經營襪廠不善,賠了大本。賣了鄉間大片田產抵債。幾乎一夜之間成了窮人。吳公館那一間她娘家的“銀行”再也無力為她支付金子了。她帶着3個兒子一下子陷入貧困。 與周揚的聯繫幾乎中斷,這期間周立波曾經從延安南下回過益陽,專程去看過吳淑媛。周立波當然不會把周揚在延安的真實情況告訴這位遠房嬸嬸。吳淑媛表示要跟周立波一起去延安。只是這個時候,她已經去不成延安了。 周立波的妻子姚陵華經常來看吳淑媛,孩子們看見她一來便與媽媽談很久。她們談的是什麼,孩子們都不知道。 吳淑媛一下子由富家小姐的位置落到平民女子的分上,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種家務來。她找來破布條打殼子,為兒子們做鞋子,親手做各種罈子菜,撲豆角、撲茄皮、撲辣椒和酸菜。這個時候,她帶了3個兒子回到新市渡蓮莊灣,周揚名下雖沒有一分田了,那裡的房子還是自己的。 城裡和鄉下都有閒言,說周揚在外面怎麼了,但無論如何吳淑媛就是不信,她根本不相信周揚會愛上別的女人而離開她,她囑咐兒子們不要聽人瞎說,“你爹爹不是那號人。” 那個時候的吳淑媛是個什麼樣子呢?她已經34歲了。我讀到周揚小侄女周舜華一部沒有寫完的遺稿,發現一段有關吳淑媛的描繪:“大約我5歲左右,我終於見到了我的嬸嬸,嬸娘與3個堂兄及保姆一行5人從城裡回到鄉下,我的嬸娘吳淑媛是益陽吳公館家的千金,愛稱嬌小姐。嬸娘長得十分美貌,高高的身材,皮膚白嫩,既圓又方正的臉盤,五官十分端正,眼睛特別發亮有神,眼皮兒是雙的,睫毛是長的,嘴是抿的,下巴稍稍前翹,她兼有東西方女子的美,她的話特別少,臉上掛着掩蓋不住的憂傷,她常常懶洋洋地倚門而立,失魂般的眼睛呆呆凝望着開井裡的茶花樹梢,一動也不動。她那倚門呆立的神情專注的樣子,真像一尊青年美婦人的雕像。”
葉夢
那個倚門望着天井中茶花樹的美麗婦人,她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她心中的憂鬱和痛苦,從不和任何人說。她這一輩子,從不和人爭什麼,也從不說任何人的壞話,即使她到死,也沒抱怨過周揚。除了母親死,她很少落淚。這位善良的女子把憂鬱這一杯毒酒留在心中獨自輕酌啜飲。不將自己的憂鬱宣泄與人,這無疑是一種慢性自殺。 有一天,正讀寄宿中學的長子艾若從學校回來,感覺周家大屋氣氛緊張。從鄉鄰到家人都在傳一張報紙,那一張報紙令全家人失色。因為那張報紙,使艾若的祖母,姑媽全都傻了。艾若再看媽媽,媽媽則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媽媽垮了。 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張怎樣的報紙,只知道那張令全家人失色的報紙透露了周揚的消息。 1996年6月我拜訪周揚的二外甥胡有萼,才知道那張報紙是桂林辦的《救亡日報》,報上登了周揚給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揚在信上談了解放區的一些情況,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蘇己進抗大,小孩己進幼兒園。” 信的末尾這一句對於蓮莊灣周家大屋,無疑是一聲晴天驚雷。 周揚的母親不知如何面對這位賢德內蘊的二兒媳。 周揚的姐姐周玉潤忍不住落了淚,她想不到幸福美滿的弟媳也重複了自己作為女人的不幸。 吳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結構的愛情童話頃刻間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張報紙否定,她沒有一滴眼淚。 從此以後,吳淑媛病了。 開始只是脖子上長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顆顆,繼之全身浮腫,臥病不起,受盡折磨。 進城看過一次信義醫院,外國醫生只搖頭,又回來了。 家中可變賣的東西不多,家人翻出幾張珍貴的火狐皮,交給本族的一個姓周的去賣,後來連那個人都不見了。 病重的時候,請一次醫生,便賣一個彩繪瓷壇,那雕花大柜上的罈子都賣光了。 吳淑媛重病的時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聲,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塊。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也不吱一聲。她的房裡靜悄悄的,像沒人一樣。 吳淑媛病危的時候,己經吃不下東西了,但想吃一種粉皮,想吃新鮮包穀,還想吃一種北方的大梨。當她弟弟吳之清好不容易托人買來一隻新鮮大梨時,她己經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臨死前的一些日子,她早已不能說話了,她望着3個兒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訴他們,又說不出來。她的意思是說那裡的東西要保管好,孩子們打開柜子,從那裡找到僅有的兩枚金戒指,這大概是她最後的首飾了。她從小穿金戴銀,不以金銀為貴。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飾都是經她的手變賣的。出嫁後,她每次從上海回來,都要從娘家帶走一批金首飾。在她看來,黃金這東西不值什麼。她己經陷入貧困多時,為什麼還會有金首飾呢?是不是周揚送她的信物呢? 在吳淑媛的病還沒有轉重的時候,有一天,正好周揚的母親、哥哥與姐姐都在她房中,她倚着床,平靜地對他們說了這樣的話:“我沒想到與運宜夫妻只有這麼久,20年真是好快,不曉得信就過去了。”當年在床前聽媽媽說話的小邁克,感覺媽媽話里一字一句都充滿着對爹爹的懷戀。她說過這些,又囑咐:“我死後,一定要給我的壽衣袖子上加上白條,我走在長輩的前面,是我的不孝。” 吳淑媛說完這些,一屋人都落淚。 她說這樣的斷頭話,是準備赴死,誰也救不了她。
奇異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東側院花圃有一叢牡丹花盛開。那牡丹多年不枝不葉,偏偏那一年突然從地里冒出來,長出枝葉並開出花來,在這院子裡長大的孩子們,只聽說這裡從前有過牡丹並未看見過牡丹,這牡丹開得有點蹊蹺,老人們則以為是異兆,深感不安。然而就在這年深秋,吳淑媛死了。 吳淑媛每日在凝望院子裡的花木時,難道她的心思都托與這牡丹花了,那埋在土裡的牡丹沉睡的根也許知道了這個女人的不幸,也忍不住要破土長出枝葉,開出一叢絢爛的花束。如果花木也能通情,那麼這一叢奇怪的牡丹開花的時候,只有吳淑媛一人知道,那花兒是為誰開的。 吳淑媛咽氣是在半夜裡,3個兒子被人叫醒,一齊跪在娘的床前。 3個兒子當時還沒有哭,母親瀕死狀態持續多日,她的死來得不突然。3個男孩的耳朵里仿佛響起了媽媽熟悉的歌聲: “小麻雀呀小麻雀, 你的母親哪裡去了?” 母親與她的歌聲飛到天上去了,她再也不會回來了,他們從此就是沒有媽媽的小麻雀了。 吳淑媛的靈堂設在周家大屋的後廳,她就躺在那一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下。那個平日裡鬧鬼的後廳,那一間孩子們白天也不敢走過的後廳,如今燈火通明。祭幛,靈幡在寒風中飄舞,3個全身重孝的男孩赤腳在泥地上,跟在道士的黑影里,圍着媽媽的靈柩一圈一圈地跑,道士們帶哭腔的長歌,深秋泥地的透骨的寒氣從腳心直逼他們的心窩。 出殯的那天,3個未成年的孩子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扶靈上山。最小的那個男孩才7歲,他們披着麻,身穿孝服。手持孝棍,孝帽上的白色棉花球在風中顫動。一時哭聲震天,看了那3個未成年的孩子,任何人都要落下淚來。周家的人更是哭成一團,崽哭娘,家娘哭媳婦,兄嫂姐姐哭弟媳。周揚的兄長周谷宜主持了弟媳的葬禮。他當時在周氏得英小學當校長,他宣布全校放假一天,全體小學生參加送殯的儀仗隊。 我於1996年元月去蓮莊灣周家大屋時,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無跡可尋。周家大屋的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一棟過去屬於周谷宜的正房。順着古老的院子牆基走,仍感覺這座院子的存在,仍感覺這片土地氤氳着一種古老森涼的氣氛。54年前盛開牡丹的那個東側院花圃,現在己是菜土了。 吳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後山,距老屋僅百米之遙。吳淑媛的墳頭長滿青草與灌木,沒有墓碑,有一塊墓碑已在文革中被人撬走。 周谷宜家佃戶的兒子卜伯藩告訴我:那一座墳是假的,真的墳己於大躍進年代被人撬開,揭去棺蓋,發現並無值錢之物之後便填平了。這一個墳堆是聽說周揚要回來,鄉里臨時做的。但地方不對,真正的墳在這假墳堆子下首3米處,那是一片白菜地。吳淑媛的遺骨在那一片水靈靈的白菜下面。冬日的陽光軟軟的,那一片無言的白菜地沒有陽光。 卜伯藩領我走一處屋檐水溝處,撬起一塊踩腳的花崗石,提來一大木桶水,衝去背面污泥,露出清晰的字跡:吳淑媛之墓。這時,那個塵封的女人便在我心中清晰起來。 卜伯藩還告訴我,1980年春天,周揚回鄉時,在蓮莊灣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當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吳淑媛墓,墓地很近,幾分鐘可達。而且已經走了一半了,吳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幾腳便可抵達。不期這時下起雨來,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個女人沒有落下的淚,這雨下得不是沒有來由。偏偏這個時候,不曉得是哪個隨從建議:下雨路滑,還是別去了吧,周揚聽從建議,退步抽身往回走。那一個墳頭那一片白菜地只是陡然地望着他和一個女人的背影離去。也許周揚不想當着眾人的面去面對吳淑媛的墓。也許他想用迴避了40多年的辦法繼續迴避。他或許沒有勇氣面對吳淑媛,哪怕只是一座無言的墓。 周揚曾一年又一年地向吳淑媛承諾暑假回來,一年又一年地沒有回來,在那個戰亂和革命年代,或許有許多複雜的難言的原因。後來周揚去了延安,延安使周揚擺脫了尷尬。這時,周揚仍給淑媛寫信,還寄去了自己新的譯著《安娜·卡列尼娜》。我不明白周揚為什麼不願意向淑媛講明實情,這裡面的苦衷,大概只有周揚自己知道。
葉夢
我於1986年10月第一次見到周艾若、周邁克兄弟時,我的第一感覺是他們像兩個少年。 我的這種直覺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一次,兄弟倆回益陽,我在朋友的晚宴上見到他們,我驚詫年近花甲的周艾若兄弟如何那樣顯得年輕。當時餐廳服務員是蓮莊灣人,周艾若激動如孩子一樣,熱情地和她談話,問長問短的,還問到周家大屋還在不? 我記得,周艾若不喜歡別人介紹他是周揚的兒子。他總要在別人的介紹之後重複:周艾若。我想:也許他不願意以父親的牌子來炫耀自己,是一種個性表現,後來才知道,不僅如此,還另有緣由。 10年之後,再見到周氏兄弟,聽他們談他們的父親與母親。在我的眼中,年過花甲的周氏兄弟,仍是一對永遠的少年,永遠的兒子。 65歲的周邁克在母親逝世後的半個多世紀,經常夢見他的媽媽,這個夢從11歲起一直到現在,纏繞他的整整一生。周邁克在敘說他的夢時,完全是當年那個11歲的孤苦無依的沒有媽媽的孩子。 眼前這個頭髮花白了的有點老態的清瘦的周邁克,就是當年那個白皮膚高鼻梁大眼睛黃捲髮的小邁克。據周家人說,周邁克酷似其母。小時候因像洋娃娃曾深得父親喜歡。 周邁克小時候很懂事,媽媽生病時,老三約瑟嬌氣,邁克趁媽媽不在,總要教訓一下弟弟,一下把弟弟惹哭了。媽媽知道後,就對邁克說:“邁克,你不要逗弟弟哭噢。” 周邁克的夢裡,常看見媽媽向他走來,媽媽還是那麼年輕漂亮,周邁克真想擁抱媽媽,但又一想,媽媽不是死了嗎?又感到害怕,夢中的媽媽講話仍是那樣溫柔,每次都說:“邁克,你乖,你要帶好弟弟,不要逗弟弟哭噢。” 這樣一個夢:己經纏繞周邁克半個世紀了。 年近70的艾若,當他唱起小時候媽媽教他唱的:“小麻雀呀小麻雀”時,流露出一臉的天真與幸福。艾若告訴我,有次,二弟邁克丟了,他報告媽媽,媽媽正在打麻將,她急得順手把麻將一推,牽起他的手滿街尋,尋到萬壽宮露天影院,她不顧守門人阻攔,不知哪來的力氣,揚手一撂,奪門而進,全然不顧很多人看她,滿場喊着邁克,當邁克從人群中冒出頭來,她跑過去一把抱住摟入懷中,這時她全身都軟了,緊緊抱着兒子,牽着艾若,喊一部黃包車回吳公館。 11歲的邁克在母親重病時,每天放學回家,遠遠望着自己的家,總是聽見那裡傳來哭聲,那是媽媽死了。他急步趕回家,這時哭聲沒了。媽媽仍無聲無息地躺在那裡,他趕緊伸手摸了摸她的鼻息。她還沒死。小邁克的這種幻覺在媽媽死前的日子裡天天重複。 吳淑媛死後,周氏兄弟在鄉間被人稱為孝子。艾若擅畫虎,好多鄉鄰都來求他畫,人們傳說:孝子畫的虎貼門上可以避邪。 纏繞在周氏三兄弟夢境與回憶中的仍舊是那個35歲的母親,他們的不可以取代的媽媽,他們不僅從她那兒得到膚色容貌,也得到了她善良的天性。他們認為他們的媽媽是世上最完美最慈愛的媽媽。 作為兒子,他們都已走向晚年,他們活了幾十年,不管以怎樣的活法,總是走不出母親的愛的濃蔭和父親的陰影。他們殘缺的童年與不完整的愛,這是後來無論用什麼也彌補不了的。 1948年秋冬之際,周艾若攜兄弟一行通過重重封鎖線,歷盡艱辛北上幾千里與父親取得聯繫。兄弟3人抵達河北石家莊出現在周揚面前時,周艾若21歲,周邁克17歲,周約瑟13歲。這是周約瑟平生第一次見到父親,周艾若和周邁克離開父親時一個7歲一個3歲。周揚見到他們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你們的母親。”周揚接着介紹:“這位你們叫媽媽也可以,叫蘇靈揚同志也可以。” 兒子們暫回到父親身邊,爾後有兩個又迅速走向自己的學習和工作崗位。留下13歲的約瑟在周揚身邊。約瑟住在文化部旁邊周揚那棟獨立小樓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有曲里拐彎的水管。兒子們走近了父親,然而又隔着一段長長的距離。
蟑螂與黑洞 這是周揚淪為植物人以後的一個日子。 看護人員休假,輪到周邁克看護父親。 躺在病床上的父親雖然活着,己經有了往日的威嚴,他的眼睛是那樣空洞而毫無目標地轉着,實際上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的頭顱、軀殼均因病變形了。 父親不像一個人,像一截變形的樹,一截永遠也不長的樹。 在周邁克的心中,父親一上像一株嚴肅的不可以親近的樹。 如今父親真成了樹一樣的人。 儘管周邁克有過與父母同在上海的幸福時光。那個時候,他才3歲,是父親偏愛的小洋娃娃。可惜那樣的好日子周邁克一點也記不起了。在他最早的記憶里竟沒有父親。關於上海的那個家,他只記得牆上掛有一架電話機。儘管他17歲以後回到父親身邊過,雖不住一起,但父子同在京城,幾十年來父子心靈上仍舊是陌生而隔膜的。 周邁克沒有想到特護病房會有蟑螂,蟑螂一到夜間便成群結隊在病人枕頭處嬉戲。周邁克不忍心讓父親遭蟑螂騷擾,試圖趕過多次,仍未奏效。趕走了又回來了,連護士也無可奈何。 奇怪的是與病人同居一室的陪人床,蟑螂卻不去騷擾。周邁克睡下的時候想,待他睡着了,蟑螂們肯定又會在父親的臉上那些鼻飼管、氧氣管之間錄歡作樂。 蟑螂是一種有思想的動物,它們不去驚擾陪床,懂得那裡睡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它們對植物人卻肆無忌憚。 周揚成為植物人,是因為腦萎縮。X光或CT顯示腦部出現一片黑洞。 我們不知道周揚成為植物人的那個確切的日子,實際上他的生命在那時已經終結。 他在跌入植物人邊緣的時候,他肯定努力為逃避黑洞而思考過。一個人在懂得思考而不能思考的時候,是最痛苦的。 這個時候,1985年元月第四次作家代表會上傳來的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那些賀信,那簽署着365位作家名字的賀信,是他一生最高的榮譽,也是他最後的輝煌。這些是對他整個生命的最好的慰安。 然而掌聲遠去之時,他早己大徹大悟,他想要重新開始,而且他己經重新開始了,他想要像真正意義上的人那樣開始自己的思考,他在生命的暮年明白到這一層,是多麼的可貴。這個時候,黑洞出現了,當他明白“時間開始了”的時候,時間卻要結束了。 可供思考的物質在萎縮,他從哪裡來還得到哪裡去。 在恍惚的邊緣人的日子裡,他是否又回到童年,重新陷入“籬棘”之中,他是否又回到周家大屋的蚊帳之內,蚊帳外的那些多腳蟲子及那些奇奇怪怪的動物又出現了。 他是否又見到了私塾先生劉宜元,先生問他的仍是關於《資治通鑑》的事。劉宜元的嚴格,仍舊使周揚生畏。 他感覺口裡是那麼乏味。他是否想起到一種吃食,那是故鄉的甘草梅子。那甜酸的梅子的記憶幾乎是刻骨銘心的,甘草梅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他是否由梅子想到淑媛,是否想吃一粒她親手做的梅子。但是他又怕見到她,在她所有青少年時代的回憶中,都會浮現她的影子。那個身材高挑,身穿黑色旗袍的青年女子披着半個多世紀塵埃翩翩而來。一口一聲“運宜”。她仍是那樣年輕那樣漂亮,她身上仍舊有那陣使人溫暖安心的氣息。他一旦伸出手,她卻飛了。她只是一個美麗的影子。 他的腦子像耗盡能量的乾電池,無力再為他作檢視一生的巡禮。腦部黑洞張開無涯的大口,一口吞沒了他。 嚴格意義上的人的生命己經停止。除了腦子,各類器官仍在工作,但不過是一架循環和消化的機器。 如此看來,作為生物機器的人和作為別的什麼機器的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能夠作為一個人活着和思考着,這多好哇! 從開始到結束,很長很長,卻又很短很短。35歲的吳淑媛與82歲的周揚在天堂相見的時候,他們會說一些什麼呢?我們自然無法知道。
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科院院士。
主要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翻譯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出版有《周揚文集》。 1989年7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5: | 血緣: 第八章 惡有惡報幾多難 (2) | |
| 2005: | 人生百態(六) 誰是過客 | |
| 2002: | 殘酷的溫柔--讀《石城海棠開》 | |
| 2002: | 同居時代的快樂與恐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