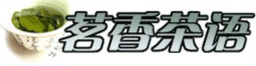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閒話曹操 |
| 送交者: 快刀丁三 2002年12月06日15:16:13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白臉、一道直衝髮際的紅、狡詐、“奸雄”、丞相、“挾天子而令諸侯”……這幾乎是所有老人、鄉村土秀才、開蒙學童眼中最早的曹操。在戲台上,曹操的戲份總是不重的。老生有諸葛亮,武生有趙子龍,花臉有張飛,丑戲有蔣干。最讓人尊敬的角色是關羽。乃至群英會上的周瑜,火燒連營的陸遜,也都因為年輕、“雄姿英發”,一直有着更重的戲分,更多的看客和說客。 如果有好中壞三個等級的人物劃分,那麼,蜀漢是正面,東吳是中立,曹操一派,必定是反角。《三國演義》的曹操故事,讓人印象最深的,也是敗走華容、割髯裹頭等狼狽的形象。他襯托着諸葛亮的睿智,趙子龍的神勇,張飛的耿直,關羽的忠義。總之,這不僅是一個壞人,還是一個屢屢落荒而逃的乏壞人。 是配角、反角,是“乏壞人”。最後,這個形象還是討厭的,咿呀咿呀地,他唱的都是讓孩童聞風喪膽、沒完沒了的腔調。在戲台下,曹操一出場,總有一群孩童不約而同地“唉”了一聲,聲音里有嘆息、討厭的成分,尾音總是拖得長長的,連綿成了一片。 但相對於秦檜、楊國忠等白臉人物,在鄉村戲台邊的大多數看客,對曹操似乎總恨不起來。甚至,在每個人隱略的心裡,這個人也多少是有些可愛、有些可親的。類似時遷、朱光年那樣的白面小丑,他憑空地給戲台添加了幾分熱鬧。 小時侯,也一直很疑惑,這樣的一個人,自己為什麼總是厭惡不起來?是受了大人的毒了嗎?還是因為他襯託了好人們有功? 進城後,離戲台遠了。雖然這個城市的街巷,不時也有老人過壽、祭謝土地的閩劇,乃至80年代中期,有一陣子手筆很大地要改革閩劇、復興閩劇過。作家魏明倫的《潘金蓮》被改編了,一出《門檻刀痕》則讓母親看了哭,哭了看。閩劇熱騰地和街市融合在一處。 但閩劇大抵只是女人的和青皮老漢的。即便有青壯、學生真心地喜愛閩劇,那也是不能說出口的。另外,一則戲台是臨時搭的,太小;二則很少有歷史戲;三則年月發展了,家裡有了電視機。對閩劇,我只是間或地看幾眼。 疏遠了戲台,也就疏遠了曹操。但曹操仍不時地從陳舊的鄉村和心底里冒出來。最鮮明的一次,是一遍遍讀着《笑傲江湖》的年月。看到杭州梅莊禿筆翁的書法時,我愕然地看到了“三國蜀漢大將張飛的狂草”等字樣。從此知道,張飛,未必就是那個“黑臉叫喳喳”的人兒。原來還有幾分風雅。 那麼曹操呢? 漸漸地不僅讀武俠小說。從戲劇到書本,一本6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詩詞》痕跡深重。讀到“……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時,心裡被打動了一下。正是崇拜毛澤東的日子,雖則注釋僅僅說曹操是“割據一方的豪強”,在奸賊之外,又添上了軍閥的形象。但自然地想過去,會被毛澤東提到的人物,必定是有幾分了得的。 因為毛澤東詩詞,把黃公略、柳直荀等想成了不世出的英豪。同樣,也因此活生生地讓自己相信,曹操如若是奸賊,也不是乏奸賊;如若是軍閥,必然是大軍閥。 在十四、五歲的英雄譜里,卻仍然沒有曹操的名字。 直面曹操,大約16歲。 懷着至少也是豪強、也是軍閥的夢,在一個失學孩子至羞澀的零花錢里,擠出了一套《三國演義》。過去幾年並不是沒有讀過,但許是書來得不易罷,首先是愛上了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忽略了呂布的下作,僅看到他的勇猛;忽略了劉表的無能,憑空去想象他“八俊”的面貌;忽略了袁紹的小氣,仿若他會盟英雄的氣勢,貫穿了他一生的風骨。 同時也在舊書攤上淘貨。《中國小說史略》評介:“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夠肥己處便肥己;他們又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夠稱尊處便稱尊”。卻正是有意疏遠魯迅的時候,並不以為然。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好!在四本古書裡,這是最有風骨最有氣力的一首詩歌。隨後,是天象的大變,盜賊的蜂起,國力的疲憊,政局的動盪。“無謀何進做三公”,不盡狼煙西邊來。三個卑微的青年尋找出路,桃園裡的聚義,都是我熟悉、喜歡、嚮往的畫卷。 到曹操出場,就多少有些讓人鄙夷了。先是不顧場合地指點人事,被轟出;再是當了一回拙劣的刺客;而後是逃亡、路見陳宮的故事。 這是一個無力、用盡小聰明、上竄下跳、自以為是的倒霉蛋。這就是曹操。 在流亡中,他以怎樣的風骨和形象激動着陳宮,讓陳宮去拋棄官職和家庭?他為什麼一副毫不掩飾的、活脫脫流氓相地放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他自幼狡詐自私,怎麼又在20歲的時候,以“舉孝廉”的道德面孔步入仕途?他更多地是文士,但怎麼那樣激烈地要去當一把刺客? 一個深夜,閒閒地又翻着《三國演義》的時候,這樣的一些念想突然冒了出來,並且不可抑制。 一個頑劣、熱中小聰明的孩童,怎樣在幾年時間裡搖身一變,強逼着自己走“舉孝廉”的路呢?在手上略有權力之後,又怎樣多少令官場老手恥笑地、有些天真地設五色棒,去整飭小城風氣呢?在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時,他為什麼依然天真、依然不世故地要以一己身軀,去博取一個刺客的聲名呢? 這樣的路途和人生,使他30歲的那個夜晚,那個震世駭俗地喊出“寧可我負天下人”的夜晚,顯得更加的煙波詭異。我看到了一個分裂的曹操。 在意想中,似乎目睹了曹操與陳宮的辯論。 真亦假;如果說這是欺世盜名,那麼,世原本可欺,名本來即盜。 陳宮說:你只有一點忽略。忽略的卻是至大的。那就是天地自然的本體,萬世不替的法則,那就是道義。你關注的是你個性的張揚,我關注的是道義的傳承。道不同,不相為謀。 曹操說:在行刺的剎那,我頓悟的,正是沒有天的不變,道的不易。我發現自我為人,蔑視的就是道貌岸然的劉漢面譜。在歲月的流逝中我不斷湮沒,又皤然頓悟。我堅信的是奉天承運。我個性的張揚,正因為我與劉漢的格格不入。 陳宮說:你成則為奸雄,敗則為小丑。 曹操說:我成則可數風流,敗則亦為俠客。 隨着陳宮的匹馬出走,這一夜,與曹操決裂的,不僅是陳宮,還有劉漢400 年的衣冠頂戴。這是一種人生的自覺,但無奈,他只有自己一個人,要一個人去與400年傳統,千萬民眾去抗衡。 張揚個性的代價便是如此。 這一夜後,曹操複雜了。 在家鄉譙縣,數百子弟被他召集到祠堂。這是劉漢傳統的棲息之地,親族與血緣也是。數百子弟中,有腦後長了反骨、認為天下不可無曹操的曹洪,但也有處世謹慎的曹仁;有一心救助劉漢的知識青年,也有單純暴躁的尚武農夫。 在祠堂,曹操一定發揮了他天下無雙的辯才,使各各不同的數百子弟,簡單紐帶在親族的香火中。另一面,曹操戲弄了一回他所置身的祠堂,曹洪受他的派遣,去匯合多少年來他羞於啟齒的另一家族夏侯家。 血緣與歸屬在這裡匯合,化做權力;生與長在這裡匯合,化做一個獨立的人。然後,他引領着那些混沌未開的青年,開始了自己一個漫長的遠征。 一路上,盜賊、農夫、流氓、義士、知識分子、舊官軍、小商人、秘密會社成員……不斷地加入這個隊伍。隊伍日漸龐大,也日漸複雜。但他總是自信,自信在這一千華里的路途中,他能夠改造、融合這個隊伍,使它變成自己意志的延伸。 隊伍有幾千人的時候,血緣、親族歸屬、義氣、個人魅力、乃至提前的封官允諾,都不夠用了。如何凝聚自己的隊伍?他輕率地也打出了“匡扶劉漢”的旗幟。 他要借傳統的旗號,去做奉天承運的事情。這正是令陳宮憤怒的地方。在短暫的平衡後,衝突的一生又展開了。對曹操,這註定了,衝突是他的常態。 這一夜後,曹操也純粹了。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的時候,確乎,對於劉漢傳統,他還有留戀,還有信任。在峨冠頂戴、仁義道德的說辭中,他也質疑過自己是不是一個流氓。但“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的道路上,偏偏又只有他這個流氓,才略具一些俠客的氣概。 他輸掉了幾千人,但贏得了徹底的自覺。很好,很夠。 個性的張揚,需要實力的奠底。在大化籠罩而又心照不宣的劉漢傳統殘餘中,實力才是硬道理。短暫的時間後,他找到了一個優良的平衡點剿滅邪教。 百萬邪教在幾月時間被蕩滌一光。30萬降匪成為部隊的主力,並在他的意志下,被重新訓練。但僅僅是為招兵買馬嗎?從安徽到山東,他不斷地回想自己和陳宮的對話。我是為大道,還是為權力? 從安徽到山東,一千華里的行軍,如果說原本,在祠堂的誓師與出征,確乎只是為權力的話,那麼,行程的目睹,則讓他發掘出了壯麗的悲憫。他寫出了“生民百遺一,念人斷人腸”的樸素情緒。 他以送葬的輓歌為載體,只有《韭露行》、《蒿里行》這樣的標題,才能負載浩劫一般的史實,自己傷時憫亂、大悲大痛的心境。 這不僅是生民的輓歌,留戀傳統時代的自己的輓歌,也是劉漢傳統的輓歌。 在文學的形式下,自己一生迷茫的“大道”,漸漸明晰。原來,陳宮的質疑是可以不去理會的。千秋功罪,誰能評說?道在生民,道在自己,結合生民與自己的,是個性的發掘和張揚。僅僅如此,如此而已。 他的目光更加樸素,更加平等。他寫《苦寒行》,目光透過大雪紛飛的太行山,不拘泥、不掩飾自己盼望回到平安喜樂日子的凡俗慾念。他照拂着一個疲憊之至的少年士兵,似乎望見了遊戲好事的往昔自己。他寫《卻東西門行》,關於征夫、行役、思鄉、盼歸,以最深切的同情,去注視着那些螻蟻一般的人群。 一路地走和征戰,直面的,除卻山河、蒼生,就是自己。而不需要幕僚、手足、妻子、文友這樣的媒介。他走過苦寒,獲得大道。他成為一個異端的志士。 在手握重兵後,他就以令人不能容忍的惡劣,去凌辱劉漢傳統,去讓自己成為不世出的奸雄。這是對陳宮們的輕蔑和諷嘲。 “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不是對劉備的抬舉,而是對自己處境的敏銳。劉備就是他一生必須面對、必須作戰的傳統的化身。於是,儘管小氣、腐朽、虛偽、混雜着道義與無恥,卻仍然強大。他自信,然而也知道,憑一己之力,他也有可能被湮沒在這樣的背景中。 於是,他不殺劉備。他把劉備當作一個對手,而對手,是必須尊重的,也是必須在人生與歷史的角斗場上去殺死的。 但在青梅煮酒的菜園,他還是要告訴劉備:你不如我。 “挾天子、令諸侯”,姑且不論政治上的深謀遠慮,至少也是一個讓陳宮、劉備們有苦難言的惡作劇。是一個辛辣到盡頭的諷刺。所有的面目與畫皮在這裡被盤剝乾淨了。 盤剝後,他就贏定了。這是一種心理的贏。是自信。自信加刀,是真正的天子之劍。 他的謀士程昱,與他一樣,在官渡決戰開始前,就以“十勝十敗論”,預言了中原的歸屬。 這是人對靈位的勝利。 官渡決戰,決戰官渡。在那狹窄的平原、河谷間,幾十萬疲憊的生民對峙着。 但所有的精彩,事實上都在他一個人獨處與煎熬的心中。在從驕傲的無賴到冷酷的決心中。甚至在他惡毒的“借頭收心”計策中。他知道這會被後世的劉備陳宮大書特書。但無所謂,莫非你們沒有借過頭? 五千子弟在他的馬和劍的引領下,以火為輔助,讓七萬人席捲了河北。 河北後,輪到了安徽、蘇北。 他尊重劉備,但他憐憫陳宮。於是,在蘇北,他痛快地讓陳宮去死。讓他一死以了結擺脫。 飲馬處,已是長江。 北方的生民漸漸攏聚,生產漸漸恢復。官田民墾,讓北方又開始有了人煙。 在漠北遼東的朔方征服中,他是否面臨過愛情,或者是單純的色慾?那個鄒姓寡婦,使他失去了長子、愛侄、侍從、馬匹。但他似乎沒有後悔過。 是愛情罷。不久以後,他讓自己的次子,也娶了一個美麗的寡婦。 古代大人物的愛情,總是這樣的淡,總是只有三兩句話、很容易讓人忽略掉的痕跡。然而好色的名聲傳揚着。蒼蠅和書蟲,總是以這樣的名義,詆毀着一個獨立的人。 是愛情罷。不久,他似乎孤獨了。這是一個征服四野、功業風流的人,一個愛人已遠去的中年男人,凡俗的孤獨。 孤獨不可怕,然而高處的寂寞,卻吞噬着他健壯的心。他需要朋友,也需要文學。只有這些,能讓他擺脫寂寞。於是,他寫出了《短歌行》。 畢竟是中年了,在15年的征戰中,又見多了離別和死亡。此時,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着自己的生活。 在舞女、文學、朋友與白酒的氣息中,他感慨、徘徊於對人生的留戀與對死亡的探究中。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世背景下,一面是“慨當以慷”,另一面是“幽思難忘”。他感傷而惋惜。於是去尋求這人間的物證。 他先是以為這物證是酒。“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但酒畢竟只是使他短暫地迴避了那幽思、那死亡。酒,並不是物證。 於是物證就轉化成了友人、知音。在友人和知音的伴同中,或酒、或音樂、或文學,那瞬間永恆的感動滿足,是不是人間的物證呢? 其實他依舊懷疑。但,這是他喜歡、熱愛的生活方式。“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即便友人和知音更不時地喚醒自己的幽思,讓自己“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但它畢竟是極致的歡樂,是顛峰的感受。 於是,他謙卑了。他尋求天下文學之士、抱負青年的聚集。他要不斷地感受那極致那永恆。一個人與自然對話的情境,畢竟是青年時的。 許多人把《短歌行》當作曹操尋求羽翼的篇章。其實,權勢的功利,斷然不能締造這樣的千古美文。源於自己的高處不勝寒,源於時光,這才是《短歌行》。 以鄴下為中心的文人集團,漸漸形成了。 在鄴下,漸漸嶄露頭角、並成為文人集團中心的,是他的兩個兒子。此時的曹操,一方面是統帥,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他關注着孩子的胸襟、抱負、追求。或者,這是因為對那樣的男人來說,當直面死亡後,繼承,已經成為康健人生的目標? 大多數庸常的人,只能追求血緣的繼承;然而對於曹操來說,血緣之外,應該有人格、意志、思想乃至自己對宇宙萬物對文學這種表達形式的傳承。是生的面貌,在後來者身上的傳承。於是,他時常詢問幾個兒子的志向,何為文?何為將?何為人? 在迷惘的青年,孤獨的壯年之後,他來到了豐盛的晚年。鄴下文人集團確乎是他播種的種,也為他帶來豐碩的果。這裡不僅是什麼蔚為壯觀的“建安文學”的圖景,不僅是使文章真正地成為“千古事”的傳奇,還在於他,曹操,一生始終年輕地、在“契闊高談”中活潑潑地、滿是生機與激情地面對暮年、達到頂峰。 不久後,他寫出了《龜雖壽》和《觀滄海》。 《龜雖壽》從對功業的蔑視,到對生活方式、極致展示自我的肯定,折射出了一個偉烈丈夫的積極與滿足。還有傷感,那傷感仍舊是發端的情緒,是對自己一生功業“騰蛇”是他的自喻終究化作土灰的傷感。但傷感畢竟已經漸漸淡去,他,仍然“志在千里”,仍然“壯心不已”。 蔑視功業,因此也蔑視自己多少小兒女形態的傷感。這就是此時的曹操。然而不僅於此。“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這說的何嘗是身體的保養,對長壽的追求,這說的何嘗不是繼承?身軀化做土灰,然而自己未必,精神與魂靈未必,風骨與人格未必。 對蒼茫的宇宙,廣漠的人間,當有了這樣的心境後,他感激、滿足、謙卑。他“幸甚至哉”,於是,對《龜雖壽》的最初傷感,反覆探求,也就變成了“歌以詠志”。 詩就是歌。這樣的曲折明朗里,我讀到了曹操雄健的人生解釋。 然而還沒完。他還要上詢星漢,下問滄海。他還要讓自己與自然萬物交流融會。於是,一種老莊失之大氣、孔孟乏其寥廓,後儒較之拘泥陳腐、今人較之淺薄寒磣的通達與神采,最終在《觀滄海》裡得以歸結。 觀滄海,在大部分曹操的詩篇中,我是較晚喜愛這一首的。它太蒼勁有力,同時缺少了一些建安特色的淺顯通俗;它幾乎沒有再創造的痕跡,沒有建安結構的以直爽為面貌、以精巧大氣為神韻的特徵。似乎,曹操老了,見得太多了,想得太遠了,功業也足夠了。此時,他只能以直觀的素描,輔助以晦澀的感悟,去表達自己對自己一生、對人生的理解。 它太直觀。“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幾乎沒有任何賦比興的技巧;它太隱略,幾乎沒有對“滄海”景象的描寫。而在一個日漸積澱了審美知覺的後世,景象與感受的融合,幾乎是不可切割的。 但這是有關宇宙人生、自然個體、素描感悟的大氣詩篇。是的,它擯棄了曲折反覆的心態與感受描寫,但底下潛流的,是空明的自我肯定;它缺少傷感樸素的人間留戀,但有關自己一生的,有關自己與自然、星漢、滄海匯合的,是他那海一般的襟懷、天地一般的感觸,最直接有力的筆觸。 他有意淡化了人間、傷感。但沒有淡化的,是自己這個一直重視的個體。是天地,這個始終身處的存在。在這裡,它們融為一體。 公元220 年,在許昌日漸繁華的街道上,小商人、走卒、衙役、農夫、無事的老漢和生非的青皮,都在悄悄流傳着一個消息:那個奸雄,死了。 散布在城中的間諜,也以加急公文的速度,把消息傳遞到建康、成都。 浩大的葬禮被迅速地籌備着。但除卻鄴下略有傷感、魏王府幾人哭泣外,葬禮雖然奢華,卻沒有多少悲痛。 或者,這也是這個從前的頑童、孝廉、刺客、流氓、豪強、詩家、哲人所盼望的? 死,對於他來說,實在只是步入那萬物的循環。哪怕一生所計劃顛覆的劉漢傳統,最終失敗,也是不足惜的。正是在這樣的路途里,他終於成就了自己,成就了風流。 這一天不知道是春和日麗,還是狂風暴雨,畢竟也只是一個在人間的、凡俗的人物的死亡。他牽引不了天地的反應。但後世的史家,大多慶幸於他的死。於是,這變成了一個大歡大喜大慶大祝的日子。 於是,在後世的戲文里,他也就變成了一個白臉的、多少被戲說的、點綴的、有些可笑的人物。 他或者能預料到?甚至,在他和陳宮對話的那一夜,就預料到了?那時還不過30歲的年齡,還對人世和歷史有着許多幻想。但真的,那時起,他就不在乎了。死去何所道,托體共山阿。何況評介?何況鄉間的戲台? 他有過程,有自己,夠了。 他源於高度的自信,並精於其道的自覺。夠了。 大丈夫,當如是! |
|
 |
 |
| 實用資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