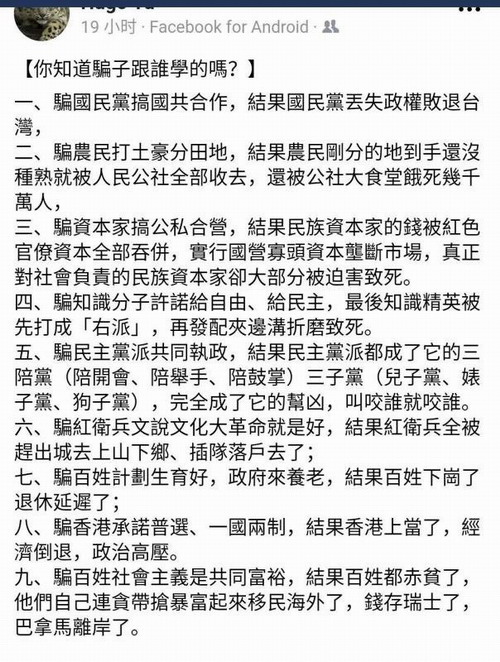| “在”與“不在”的世界 |
| 送交者: 李亞軍 2018年12月27日01:22: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陳行之 長期以來我對天文學始終懷有濃厚興趣,在為數不多的藏書中,竟然有數十本這方面的著作,我覺得夜深人靜之時徜徉在浩瀚無垠的宇宙星空之中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興趣僅僅是興趣,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就此寫什麼東西,讀者正在閱讀的這篇東西也不是,借題發揮而已。 1 宇宙學有“暗能量”概念,這個概念最早緣於愛因斯坦的假設,當時並沒有被證實,後來,愛因斯坦本人認為這個假設是一個錯誤,原因竟然不是科學的而是審美的:因為它破壞了廣義相對論的優美性。萬幸的是,這個假設沒有隨着愛因斯坦的否定而退出人們的視野,暗能量問題始終是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關注的焦點,成為了現代宇宙學和粒子物理學的重要課題。 一般認為,暗能量占據宇宙三分之二的比例(已經得到了證實),這就是說,對宇宙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我們悉常觀念中的物質,而是一種看不見、摸不着,卻具有極大能量的東西,與物質相對,被稱之為“反物質”、“暗物質”,它們產生的能量,即為“暗能量”。暗能量如此巨大,我們為什麼感受不到呢?科學家解釋說,在任何一個給定的空間裡,反物質的能量都很小,因此它在我們日常經驗中是不無法被感覺到的,但是在廣漠的宇宙空間,它們的效能卻非常非常大,大到使星系和星系簇分離、甚至決定着宇宙樣式的程度。 “宇宙的樣式”對我們有意義嗎?當然有。從純科學角度講,人類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肉體不過是化學現象中的原子聚集而已,本質上與一個蘋果、一個土豆沒有太大的區別;我們的呼吸、運動和所有生命現象都是自然存在的一種方式;我們被包含在宇宙之中,與宇宙運動息息相關,從根本上說來,是宇宙的樣式(或者說規律)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決定着我們的生命狀態,只不過這些東西與直接構成日常經驗的柴米油鹽以及各種精神活動距離過於遙遠,很少有人將其與自己活得如意還是不如意聯繫起來罷了。 怎麼想起宇宙學來了呢?緣於一種啟示。 2 我們都知道,社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思想、行為表現結構而成的,任何個體行為都應當被看成社會群體行為(或者說社會運動方式)的特殊表現,在一定意義上,人的社會生命起源於與他人的交流,當你在生命史中發現社會性的時候,也正是你發現個性的時候,反之亦然。人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個體存在,即使是在人煙罕至的孤島上,他也一定通過遺傳與社會緊密相連,人在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確立自己的本質……既然這樣,對於塑造我們基本人格、決定我們精神形態的那個“社會”,就應當給以切實的注意了,就像天文學家研究星體必須着眼於容納那個星體的宇宙一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我們都是社會宇宙中的星體,決定我們狀態的,既有被我們的經驗所證實的東西,也有我們未曾經驗到、卻無時無刻不對我們的內在命運發生影響的東西——和宇宙學中“物質”與“反物質”一樣,我們作為一粒顆微不足道的宇宙塵埃,同樣面對着兩個世界,這就是本文標題所示:“在”的世界和“不在”的世界。 這話又是從何說起的呢?1968年年底,文化大革命最為瘋狂的階段已經過去,這場造成巨大人文災難的政治運動對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開始顯現出來,一個突出表現是就業崗位不足,城市無力消納每天都在增加的就業人口。這就是說,當局面對的是一場由其自身荒謬的政治行為導致的社會災難,如何消弭這場災難,恢復舊有秩序,重新獲得對社會的控制,把問題解決在更大的問題產生之前,就成為權力者不能不優先考慮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健康正派的社會,媒體會告訴公眾這個國家究竟遇到了什麼問題,公眾會對權力者的執政能力和政治品格提出質疑;工會等民間社團組織會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與資方博弈,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政府會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在均衡中向前發展;民眾會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權力者會被民眾詰問乃至於反對,在全民公投、全民普選中,權力者也許會光榮或者不光榮地失去權力,譬如總統被彈劾,國會被解散,某些政治品德低劣的權力者還有可能受到法律追究,被審訊被逮捕直至被投入監獄……我不敢斷言這是歷史規律,但是至少可以認為,所有正派國家都是在這樣的社會過程中走向完善的。 如果我們親愛的祖國也是這樣一個正派國家,那麼,1968年年底就應當發生這樣的事情: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告訴公眾,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究竟遇到了什麼問題,連篇累牘報道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狀況,人民應當對黨中央、毛主席的執政能力和政治品格提出質疑;散布在各行各業的工會及其他民間社團組織代表不同階層與權力者博弈,使權力和權利在博弈中達到均衡;政府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在均衡中向前發展;民眾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在這個過程中,黨中央、毛主席很有可能被民眾詰問乃至於反對,在全民公投、全民普選中,他們也許會光榮或者不光榮地失去權力,譬如毛澤東被彈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解散,某些政治品德低劣的權力者(如“四人幫”者流)還有可能受到法律追究,被審訊被逮捕直至投入監獄……我當然不能斷言國家通過這樣的社會過程一定能夠度過危機,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生活在真實中,即使是危機也是可見可感的,我們也沒有失去官能,我們在與世界的交流中確認自己,我們“在”在一個“在”的世界,我們作為祖國的公民能夠為度過危機做我們能夠做到的一切。 然而,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了呢?我只說直接感受到的東西。 3 1968年12月22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意識形態喧嚷之中,《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援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旋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在全國如火如荼展開了,一個龐大的待就業群體(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中學畢業生共計1600多萬人,幾近於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一夜之間突然改變生活軌跡,浩浩蕩蕩離開城市,進入鄉村。我作為這1600多萬人中的一員插隊落戶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從而成為了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儘管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遷徙運動是統治集團對社會經濟危機做出的被動甚至可以說無能的反應,卻被冠以了一個高尚的政治名稱:革命。沒有在那個年代生存過的人很難了解體現國家意志的“革命”這兩個字的份量,它是一種超級存在,一種橫亙在人們靈魂原野上的野蠻事物,在它面前,任何個體的渴望(吃飽穿暖的渴望,愛情的渴望,精神發展的渴望)都會成為非法,它不但不允許你言說,它甚至讓你覺得想一想都有罪……我們說極權主義具有一種對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的特性,指的就是這種對個體渴望的壓制乃至於毀滅。 當對學校進行管理的“軍代表”帶領我們學習毛主席他老人家偉大指示的時候,當延安地區官員在北京各所中學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說紅色延安如今猶如天堂一般美好的時候,我們這些失去選擇的選擇者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呢?我們只能“滿懷革命豪情”地去報名插隊落戶,只能“意氣風發”地離別親人到那塊陌生的土地上接受“革命洗禮”,渴望子女留在身邊的母親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流淌眼淚,幾乎還是個孩子的女兒也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偎依在媽媽懷抱里表達對未來的恐懼與憂傷……第二天,紅旗照舊獵獵,凱歌照舊飛揚,鑼鼓照舊驚天動地,口號聲照舊響徹雲霄,所有的母親和孩子都得把本真深深地掩藏起來,以“革命”的姿態出現在眼前這個並不真實的世界之中——這意味着上山下鄉運動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統治者所需要的那種贊同和支撐。 四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難以忘記,當西去的列車開始蠕動的時候,當生離死別在這個沉默的群體中強調悲愴的時候,壓抑在人們內心深處的真情終於掙脫開理智的約束,迸發了出來——站台上和車廂里突然“嗡”的一下奔放開了哭聲,無數雙手伸向空中相互尋找,整個站台都隨着列車移動起來……那年我18歲,這是我第一次在公眾場合看到人不約而同地表達真情,那驚天地泣鬼神一般的哭嚎像重錘一樣擊打着我稚嫩的靈魂,從此以後,每當身邊包裹着滑稽的莊嚴和輝煌的偽善的時候,我總是提醒自己說:“不,這不是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不在這裡。” 真實的世界在哪裡呢?在“不在”之中。 4 漢娜·阿倫特不是可以草率閱讀和泛泛談論的政治哲學家,對於她任何簡單的話語,你都必須用靈魂去傾聽,只有這樣,你才不會忽略不應當忽略的東西,感受思想的無限魅力和由它所釋放的巨大熱能。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阿倫特單獨列出一章論述極權主義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極權主義國家,宣傳(propaganda)和恐怖相輔構成,這一點早已為人們所指出,而且經常被如此認定,然而這隻反映出了部分事實。凡是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都在用灌輸(indoctrination)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說是恐嚇民眾(只有在初期階段,當政治反對派仍然存在時,才這樣做),不如說是為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宣傳和灌輸是恐怖的“心理戰”的組成部分,“真正恐怖的在於:它統治的是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請注意“心理戰”和“沉默的居民”兩個概念。 “心理戰”,我理解應當是指對對象實施心理影響並進而決定對象思想和行為方式的策略,極權主義的對象是民眾,這裡說的“心理戰”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解析:是統治者對民眾實施心理影響並進而決定民眾思想和行為方式的策略,作為這種策略的結果,才是“沉默的居民”。這就是說,“心理戰”和“沉默的居民”這兩個概念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它們既是“宣傳”與“灌輸”的起始,又是它們的終結。 無數活生生的個體竟然成為“完全沉默的居民”,他們一定是失去了現實存在的世界,被另外一個與人的自然本性完全隔離的世界替代了,他們“在”在一個“不在”的世界,這個世界像化學溶劑那樣溶解着人的靈魂,使人成為“非人”,成為某種社會產品,某種物——“宣傳”和“灌輸”,這兩個看起來並不殘忍的詞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散發出恐怖氣味的。 具體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上面說到的“意識形態蠱惑”其實就是阿倫特說的以宣傳和灌輸為其主要手段的“心理戰”,權力者用強大的宣傳機器遮蔽真實的世界,用謊言虛構出一個並不存在的世界,從而製造出一個“幻境”。在這個“幻境”之中,民眾失去了對社會和自身進行判斷的條件和基準,或者說,權力者壓制了民眾對社會和自身進行判斷的能力,其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成為“沉默的居民”。 1968年那個寒冷冬季,我們正是作為“沉默的居民”行使社會角色的——我們“滿懷革命豪情”地“自願報名”去陝北插隊,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天安門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做“紮根農村一輩子”的宣誓,我們自認為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時代驕子……我們完全不知道,所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不過是一句託辭,它掩蓋了權力者向民眾轉嫁社會危機的企圖,掩蓋了權力者對民眾利益的極端漠視,掩蓋了權力者卑劣的赤裸裸社會操縱伎倆。 我們這些自認為時代驕子的人,不過一些沒有生命的“物”,不同點僅僅在於,在此之前我們被安放到了毛澤東“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的“紅衛兵小將”的位置,現在又被安放到了“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知識青年位置,不同的位置從來沒有改變我們真實的人生處境——我們只是一些“物”,是權力者可以任意驅使的東西。 雖然隨後就有《受騙到陝西》之類知青歌曲在知青群體中傳唱,然而真正洞悉我們真實的人生圖景,認識到我們真實的身份意義,卻是很多年以後了,此時,這個1600多萬人的群體已經消耗掉了青春,有的甚至把生命也拋卻在了那條漫長而孤獨的道路上,仍舊活着的,也成為了被勒令買斷工齡的人,成為了在極為苛刻條件下不得不下崗的工人,成為了擁擠在城市大雜院裡的退休教師,成為了拿到經濟適用房房號、正在為湊集房款而心急火燎的大爺大媽,成為了被子女很瞧不起、基本上已經被證明人生失敗了的父母……這就是“物”的命運。 如果把命運視為一種輪迴,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它周而復始,無始無終,昨天是你,今天是我,明天是他……只要作為超級存在的權力魔獸仍舊在大地上橫行,你我他都改變不了宿命更改變不了輪迴,道理很簡單:你僅僅是一個“物”,你面臨的全部問題僅僅是權力者將你置放何處的問題。 那麼,你現在又在哪裡呢?你在失去土地的農民中,遙望着城市和鄉村,不知道哪裡才是你落腳的地方;你在被強制拆遷的房屋裡,聽着推土機巨大的轟鳴,你只能摟抱着妻子兒女瑟瑟發抖;你在因為販賣針頭線腦而被城管人員追打的小商小販中,劇烈的奔跑使你的胸腔劇痛,喉嚨中涌動着一種令人作嘔的鹹味兒,那是你累得將要吐血了;你在幼小女兒被權力者猥褻、強姦的家長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默默地哭泣,聲嘶力竭地哭泣,捶胸頓足地哭泣……你作為“物”,所有命運範疇以內發生的事情都與你的內在本質無關,你被代表,你被捐款,你被失蹤,你被自願,你被就業,你被自殺,你被開心,你被小康……你被置放到了一個充滿奇異色彩的奇境之中。 5 是的,是奇境。在這裡,所有東西都是預先設定的,這裡的一切與世界的真實圖景都風馬牛不相及,這裡沒有“真相”——過去沒有真相,現在沒有真相,將來仍舊沒有真相,你接受和了解的全部是權力者想讓你接受和了解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本來“不在”的“在”,你的所有感官都被矇騙了。 托馬斯·潘恩論述人權問題的時候,曾經提示一個常識:“在任何事情能夠通過推考得出結論之前,必需先確立肯定或否定據以推考的某些事實、原則或資料。”(《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假若所有“事實、原則或資料”全部被扭曲、被遮掩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阿倫特舉例說,當斯大林決定重寫俄國革命歷史(這裡指的是《聯共(布)黨史》——陳行之注)的時候,他要做的首先是將原有的歷史記載、文件乃至於作者一起滅失,製造出一個歷史真空,然後用謊言進行填塞,這是一個“不在”的“在”。 奇境就是“真空”——歷史的真空,現實的真空,未來的真空。當所有這些真空都被統治者意志填滿的時候,當“確立肯定或否定據以推考的某些事實、原則或資料”全部被謊言替代的時候,人們判斷世界的基礎和條件事實上也就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只能成為“非人”……我想,這就是極權主義者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了吧! 可見,“在”並不因為它事實上的“不在”而虛弱,相反,它強悍無比,它是一種野蠻的強制力量,沒有人能夠違拗它,更沒有人能夠阻擋它,在它面前,任何個體都渺小如同螻蟻,你只能順從它,只能依據它的願望去看,去說,去想,非如此你就將“不在”——看一看周圍吧!有多少人因為恪守了良知(僅僅因為說了些讓權力者不愛聽的話)就成為了“不在”,你還領略不來作為魔獸的“在”的兇險和殘暴麼? 當國家意志成為魔獸在大地上橫行的時候,人是什麼呢?人充其量只是供魔獸蹂躪的玩偶,你作為玩偶當然既沒有意志也沒有生命。在這個奇境之中,你將面臨一個無情的邏輯鏈——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大寫的人”?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人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財產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居住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遊行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示威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結社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出版權?你連人也不是還遑論什麼言論權?這真是一個奇境,一個令人驚嘆的奇境! 我前面說過,在這個奇境之中,你不過是國家強力隨心所欲置放的“物”。“物”還有尊嚴麼?“物”還有精神發展的權利麼?當然沒有,你無須有。在這種情況下,權力者當然有理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絕不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邪路,因為你是“物”,你沒有選擇的自由,你甚至連判斷的條件和判斷的能力都喪失了,你又根據什麼提出自己的權利主張呢?正是在這個奇妙的邏輯鏈中,任何精神範疇的東西都被抽取了,你被置放的地方就是你的全部價值意義所在。 6 自然與社會在機理上是相通的,所以我們才經由宇宙學“暗物質”想到眼前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人文世界。這個世界固然讓我們絕望,但是,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我們從宇宙學中得到的啟示似乎還不僅限於絕望。 既然決定宇宙形態的是神秘的“暗物質”,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設想在人類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那種顯赫的“在”,而是“不在”的“在”呢?當歷史站出來訴說真相的時候,當謊言潰解真實顯露的時候,當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迴旋起人的合唱的時候,你——無論你是誰:權力者和資本合謀製造的下崗工人,權力者和資本合謀製造的失地農民,權力者和資本合謀製造的被強制拆遷的居民,被權力者排斥在社會邊緣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被城管人員追打吐血的販賣針頭線腦的小販,幼小女兒被權力者猥褻、強姦的家長……都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那絕不是哭泣,絕不是。 “沉默的居民”一旦發出聲音,就絕不是哭泣。那是一個從來沒有真正“在”過的群體在用整個生命吶喊。那是從來沒有真正“在”過的世界開天闢地的壯烈顯現。在這場遽烈的宇宙運動中,再專橫堅固的“在”也將土崩瓦解,新的星體將從母體中誕生,也只有那個時候,我們才會在天空和大地上看到人,看到直立的人,看到大寫的人。
|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復熱帖 |
|
|
|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17: | 耶誕節在中國早已變質,美國人有這麼荒 | |
| 2017: | 中美都說自己贏了朝鮮戰爭 | |
| 2016: | 106.大悲心依第八識心而生 | |
| 2016: | 溪谷閒人:談中國風雲人物馬雲 | |
| 2015: | 從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看建國初17年文 | |
| 2015: | 馬英九炮轟空心菜:兩岸政策3天就變 | |
| 2014: | 一位美國人眼中的法輪功。 | |
| 2014: | 警惕邪教的滲透——瑞克·艾倫·羅斯先 | |
| 2013: | 誰也無法阻止我對毛澤東的崇拜 | |
| 2013: | 芝加哥華人紀念毛澤東主席120周年誕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