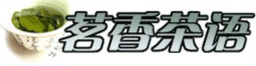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三說李安,或關於李安的說三道四 |
| 送交者: 蕭瞳 2004年11月25日11:32:0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我可以在成都三說李安,是因為他不是拍《臥虎藏龍》的那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而是一個住在中國的法國人。所以我寫他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我認識他(這是最重要的);二,他叫李安——別以為我在玩文字遊戲,要知道我們所有人(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都叫他李安,誰也不記得他的法文名字是什麼——我認為,在這點上他比前述的國際名導更為成功。另外,此李安是王小波和王安憶作品的法文翻譯者,因此可以說,此李安與彼李安一樣都是中國文化的傳播者,所不同的是此李安傳播活生生的當代文化。所以啊,沒有什麼比問他為什麼取這個中文名字更令人煩悶的了。不幸的是,李安和他的朋友們都得經常面對這樣的問題。 至於李安為什麼選擇住在成都翻譯京滬二王的作品,我很願意說這就是成都的魅力,再順便提一提他最初在川大短暫的留學生涯。實際上說他住在成都都不夠準確,他簡直是在“撫摸“成都,而且不放過任何細節。他租住的是市井民房,常遊走於街頭巷尾;選蒼蠅館子吃飯,在路邊茶鋪喝茶。時間長了,遂得一“絕”技:熟識成都所有的老街,尤其是那些已經或即將消失的。我的經驗是,越偏僻街道越窄的地方,越有可能碰到李安。他知道哪兒的啤酒一元錢一紮,哪兒的茶五毛一碗,哪兒十元錢可吃三菜一湯……,不僅如此,他還經常能得到額外的優惠,因為跟老闆的交情。當然,就訪貧問苦的卓絕而論,李安跟歷史上的傳教士相比還差得遠,但他的目的也跟他們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在李安這兒,交流、融匯的願望已取代了改造或“拯救”的激情。基本上你不會把他當“老外”,如果你認識他。真沒有誰把他當老外。在我們常去的大同路茶館,偶爾路過一個香水濃郁的女子,或扛着大包的搬運工,往往有一至數隻品種各異的狗會衝上去攔路狂吠。可是,李安就算渾身澆上油漆,把茶館的桌子全搬走,那些狗都不會吭上一聲。也許我該說說李安的長相了:身高總有一米九十幾,眼睛如阿蘭•德龍般深邃,胡茬堪比貝爾蒙多,鼻子之大可能超過德帕迪約……,總之看外表看護照,皆決無假洋鬼子之嫌。據他講,他的血統中包含法、意、英、波蘭……等國,差不多可以組建一個小型歐盟了。 這樣一個人,你怎麼看他,完全取決於你對他了解多少。 1、 時間過得真他媽快,至今我已想不起認識李安的確切時間了。幾年前,一個朋友在“波希米亞”酒吧的聚會上給我們彼此介紹,我們都說早就認識了,總是在培根路的哪個茶館裡吧。那陣子培根路上的老外和中國人一樣多,誰也不會把誰當寶貝。但在“波希米亞”酒吧那天,李安是唯一的外國人,而且身份是“巴黎來的詩人”,似乎他的到來總算讓“波希米亞”四個字落了實。這廝也端的了得,漢語流利不說,還能聽懂四川話。他端着杯子不時換座,跟男男女女各各交鋒,一晚上車輪戰罷,談了幾十個話題依然毫無倦意。子夜,在朦朧的醉意中,我記得他長久地坐在兩個女孩跟前(當然,我也恰好在一旁),神情卻真誠嚴肅,並無一絲輕浮。女孩們顧自去笑的時候,他依然專注地望着她們,臉就像電影裡的特寫鏡頭那麼大、那麼意蘊無盡。當時我想,這傢伙真厲害啊——我指的是酒量。不過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搞錯了:李安煙酒不沾,他的杯子裡裝的是水。成都的“波希米亞”酒吧里,一個“巴黎詩人”在喝水,讓人怎麼不去想“淮南為橘,淮北為枳”那句話呢。那以後,我就經常在不同的地方碰見李安。他聲音低調,穿着樸素,無論騎車還是走路,總是慢悠悠的。他的眼神緩慢地從一處移向另一處,好象什麼都沒看見,卻跟那些窮街陋巷有一種精神上的和諧。但他實在太高大了,儘管偏瘦,仍然給人以材料上的鋪張感。他站在一群圍觀的居民後面觀看110處理糾紛,他的車也突兀在別的車中間,坐墊下撐着一截長長的鋼管;而他推着那輛車走路時,你卻會以為那是一輛別人(某個女孩?)的車。如果合影,其他人還處於中景範圍,他已進入近景;坐在一張桌上,當然,他就是個永恆的特寫鏡頭。就中國人一般的審美來看,他原本英俊的外表像仿佛在放大過程中有些變形(使他像他故鄉的點彩畫一樣需要一段距離讓我們的視力去整合),因而難免令人心生畏懼。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從未見過這種情況發生。看上去李安活得很好,在越來越來多熟識他的人中間,在他熟悉的老街區,他擁有一個煙霧升騰、雞犬相聞的獨立王國,那種王國我們的下一代也許只能在網絡上尋找了。不消說,即便只過如此安貧的生活也是需要經濟支撐的,何況李安還不時在中、法之間飛來飛去——他其實擁有比他的中國鄰居和朋友們多得多的自由。但我們都不關心這個,它涉及的是一種現實卻難以馬上改變的不公。大家只是有緣坐在夕陽和夜色里,在成都最後的幾條老街上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我們下午喝茶,晚上喝酒。李安只喝茶。 成都作家汪建輝曾有妙語:詩人就是既懶而又想當作家的人。——這話本身說得也很懶,可見懶是擋不住的誘惑。我的觀察是:詩人相遇費酒,作家見面費茶,共通之處是都要經常跑廁所。如果說詩人是酒色之徒,作家也是“茶色之徒”。“巴黎來的詩人”何時轉變為一名作家兼翻譯家的,我也沒什麼特殊記憶,但我將之歸因於茶。就是在培根路的“老院壩”茶館,李安第一次拿出了他用漢語寫的小說手稿。說來慚愧,除了它的反烏托邦主題——人類克隆化的未來,我已茫然無所印象。我記得我甚至懷疑那裡面詭秘、艷麗的語言是否表達失誤所至。這樣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用酒來解釋,但我深知真正的原因在於我蔑視手稿的惡習。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漫長的遊歷中,我看過太多寫在筆記本、日記本、作業本……上的“實驗作品”,以至現在根深蒂固地認為,手稿是對讀者的一種挑釁,自信、負責的寫作者起碼應該讓人看打印稿。再後來,當我知道李安在做翻譯時,他翻譯的王小波已得到後者遺孀李銀河的認可在法國出版。我不懂法文,據他說李銀河也不懂——所以啊,望着他平靜的表情和書案上的幾本詞典,我真的很懷疑文學翻譯是這麼簡單的。直到我讀到了李安發表在一本內部交流資料的上的小說:《屠夫》。那是一本純文學民刊,印量很少,但編輯顯然意識到了作品的分量,將它排在小說類的第一位。在主標題下面,作者謙卑地加了個副題:“試圖描寫”。說實話,它讓我為許多時下的小說寫作者感到汗顏。倒不是說這篇不足萬字的練手之作有多大的開拓性、觀念有多麼的新(這些東西真有那麼重要嗎?),我驚詫於它語言的精純、文體的成熟和形象的斑斕。一個外國人,沒有任何機構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可能“毫無利己的動機”。但他學習我們的母語,他對語言技術的精益求精,“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是個極好的教訓。”* 注再說啊,語言對於一個人真的可以只是技術嗎? 2、 幾年前,一個德國女孩對我說,到中國學習漢語的西方留學生分為兩個陣營,其標誌是對中國公廁的態度。忍受不了中國公廁的人會隨時抱怨,其中不少人很快放棄學業及整個中國;另一個陣營的人對此嗤之以鼻,並且說,我們到中國不是為了上廁所。(難怪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氣味相投”這個詞,鼻子自古就與外交有關。)李安從沒對這個問題發表過看法,但他比我們認識的絕大多數老外在中國呆的時間都長得多,而且還沒有要離開的跡象。為重新簽證、為在法國出版譯著,或只是旅遊,他會短暫地消失一段時間。他重新出現在老地方時,並沒有誰驚訝,他不過是“出去”又“回來了”。就單純的“氣味”而言,李安比大部分中國人都更有“中國味兒”。他身上終年飄蕩着各種中藥的香氣,還不時往嘴裡扔進幾粒新發現的苗藥、藏藥……,有些我們簡直連名字都沒聽說過。 還是那個德國女孩說,她沒見過一個男老外不喜歡中國女孩的。(當然,這很難成為他們長期滯留中國的原因。喜歡歸喜歡,多久和多少是另一個問題。)我的印象里李安總是單獨出現,也單獨消失。起初,你會覺得他熱衷於和女孩子長談;可很快你會發現他跟每一個想和他說話的人長談,除非你試圖跟他講英語——這種時候,他會非常誇張地說:“我聽不懂英語,我不是英國人,你也不是,為什麼和我說英語?”有一次在他水井街的家裡,他終於提到有一個中國女友,我們都有些驚訝。她遠在麗江,我們都沒見過。“我太大了……”李安邊說邊觀察着我們的反應,語氣中竟有些許悲哀。他說每當他和女友一同照鏡子,他都為自己的巨大而感到“有點可怕”。大家都笑起來。我突然想起他弓着背在街巷裡緩緩穿行的樣子,他的舊自行車和灰撲撲的穿着,他的“中國味兒”,完全是在煞費苦心地試圖融入周圍的牆壁和空氣。 那次在李安家裡,我還看到了一件意外的東西:一個寫着大大的“茶”字的木製招牌。它來自我們熟悉的“老院壩”茶館。當時那裡已被拆遷,只剩一片瓦礫。與文里、培根路一帶拆掉以後,有好幾個月朋友們沒有合適的聚會場所。誰都沒想到,新的地點是李安“提供”的,他已經在那一片住了好幾年。那也是一個註定要被拆遷的區域,我們第一次在那兒喝茶時,它就已經被一道延綿數里的華麗仿古長牆團團圍住了。考古發現證明,這裡是世界上最早生產白酒的地方,重建只在早晚。問題是,李安已經把這裡當成了他的家。他真是使用的“家”這個煽情的詞,而茶館的主人,就像他“家裡人一樣”。他長期在那兒喝茶吃飯——當然,是付錢的。漸漸地,大家發現李安改變了他沉穩的做派,甚至停下了手頭的翻譯。他開始主動向他認識的每個中國人詢問對拆遷的看法,並整晚整晚地討論。如果你同意他的看法,下一次見面他的開場白就是,那裡那裡又拆了,你知道嗎?然後沉默地望着你,你就有了一分罪責;如果你和他意見不合,那他那種不加掩飾的失望會令你感到空氣收縮。有一次他竟利用帶路上廁所之機誘拐一個剛認識的女孩,跟他去看一座新建在附近河上的巨大石橋,目的是說明它有多麼丑,因為橋上沒給窮人留什麼位子。另一次,在回了一趟巴黎之後,他告訴我們,他老是夢見中國人在拆巴黎的房子。“他們已經在拆,是溫州的,他們嫌服裝店的門臉太小……”。他說這些的時候聲調依舊低沉,但目光灼人,表現得非常固執,與他“固執”地認為自己不懂英文有本質差別(真到了有人需要幫忙的時候,他的英文沒有任何問題)。若依保守的中式標準,這種完全出於情感的孩童般的固執與他消匿於市井人群的初衷背道而馳,也跟他“不惑”的年齡靠不上譜——我似乎一直在有意忘記介紹他的年齡,因為這跟他留給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在一個普遍比他小不少卻日益中年化的圈子裡,他是個“沒有年齡的人”。自然,李安也有他的限度,或曰法國式的圓滑,總不至於將他人和自己逼到非此即彼的地步。在這個面積每天都在減少的“王國”里,李安式的傷感也總會被嘲笑與自嘲稀釋掉,隨着殘茶潑灑在廢墟旁,無奈地等待機器轟鳴的逼近。總的來說他與所有人都相處融洽,也沒有人為難過他。我印象里真正尷尬的事只發生過一次。那天他被迫參與玩一種集體性酒令。作為不喝酒的懲罰,他必須唱法語歌。短暫地默想了一下以後,懷着一不做二不休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激情,李安起立大聲唱了起來。但他雄壯的的歌聲馬上就被另一種更響亮的聲音壓倒了——那些從沒聽他說過法語的狗集體狂吠起來。 3、 法語。 巴黎。無論有多少或真或假的知識分子將法國視為精神上的祖國,它對於我們依然遙遠。算起來,李安到中國時已三十出頭,而他那屬於遙遠國度的過去是我們所難於觸摸的。李安並不迴避談論法國和往事。比如,我們知道他最喜愛的法國作家是福樓拜和普魯斯特,他參加過巴黎市民抗議新納粹的遊行(口號是“我們都是雜種”),等等,諸如此類,我們在書本和電視裡已經知道的東西。此外我還知道他過去是喝酒的。不但喝,而且喝很多;他也抽煙,不但抽煙,還抽大麻。他指着他的心口說:“這裡面全爛了”。有一陣,李安決定吃素半年,“給身體打掃衛生”。他想清理些什麼呢? 在一次完全偶然的聚會上,我聽李安講述了以下他最為的驚人的故事:巴黎某夜,李安路過一家他常去的酒吧(“我跟他們非常熟,真的”)。那裡熱鬧非凡,因為晚上有活動(“這跟中國一樣”)。門口擠滿了排隊買票的人(“這也跟中國一樣”),有保安在維持秩序(“巴黎也有保安”)。李安決定從一個側門溜進去看看就走,但他被發現了(“我想沒有任何問題,他們一直喜歡我”)。一個黑人保安被叫過來時,李安還在笑(“我並不害怕,因為我知道他們喜歡我”)。那個保安非常高大(順着李安舉過頭的手我看到一盞昏黃的路燈),他一句話都沒說(李安眼中現出了恐懼),就一頭撞在李安的臉上(大家都把頭往後一仰)。李安捂着臉跑到醫院(“非常疼非常疼……除了疼還有生氣”),他的鼻梁骨斷了。李安講述這個故事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安慰一個剛遭受過保安欺凌的朋友,並證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被壓迫”這個普世真理。但這個故事裡的某種色彩觸動了我,我翻出李安的小說《屠夫》。《屠夫》以巴黎為背景,主角是一個以肉店為舞台的眩目女店主。在描寫女店主的穿着時李安寫道: 打扮。衣服上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中間卻賤得滿是紅斑點,很像某夜我進急診室,鼻梁骨折、腮幫腫脹並且在頭昏眼花下見到幾位忙忙碌碌的護士的外科制服上陰陽怪氣的棉紗血衣…… 噫?在小說結尾,女店主似乎跟人私奔了,同時敘事者又虛構了一個她暴死在家的情節(“已經死了幾個月了,屍體保護得完美無損,嘴唇還紅潤,好象還有什麼話要說……”)。敘事者解釋說,這樣“或許能將她從終生的虛偽中拯救出來”。——這裡面隱含了一個絕望的愛情故事嗎?莫非女主角慘遭虛構的原因就隱藏在小說中那句看似漫不經心的“我看她不是特別喜歡我”中?(請原諒我這種不負責任的捕風捉影,但我想大部分的文學想象正是起源於此。)我不知道。就李安駕御複雜文體的能力來看,這不大可能是百密一疏的真情流露反倒像有意賣出的破綻,精心設下的圈套。所以啊,我以偵探眼光重讀此書的結果只是失望地發現,在李安以第一人稱進行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描寫中,我們對巴黎和他本人生活的了解並沒什麼增加。其實這是一個被“懸置”起來的故事,它獨立於周圍的時空,幾乎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那為什麼不是在中國呢?《屠夫》是我迄今看到的李安最成型的漢語作品,寫作於他與成都生活已經水乳交融的時期,他完全迴避了這個背景。關於中國的一切只會出現在他的法語作品中嗎?還是即便對於他,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多年的人,所擁有的也還只是無法言喻的迷濛,一如巴黎之於我們? 最後值得一說的是最近一次見到李安的情形。那天是他的生日,李安在即將消失的大同路茶館大宴賓客。來賓有中外男女二、三十人之多,對坐在七、八張拼成一字形的茶桌兩邊。有人不合時宜地想起了“最後的晚餐”,但無論如何,這樣的盛況不同尋常。地道的家常菜兵分幾路端了上來。好幾種語言雜唱生日歌之後,在眾目睽睽之下,李安接過滿滿一杯啤酒……幹了。
*註:毛澤東:《紀念白求恩》 |
|
 |
 |
| 實用資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