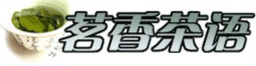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我們和我們所相信的力量 |
| 送交者: 葦浦麗薇 2006年03月30日06:25:27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讀後 2003.2.22 一. 在那個年代還沒有“科幻小說”這個類別,直到一百年後人們說,它就是科幻小說的開山鼻祖。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小說被太多次地拍成電影、舞台劇等各種表演形式,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它都未能逃脫“恐怖電影”這一仿佛是必然的命運。對讀者來說,簡單地稱之為“哥特小說”也許不失方便和貼切。 它的出名被認為是因為作者的身世。因為作者的父親母親都是出名的文人,並且更為出名的是她的丈夫,舉世聞名的著名詩人。在這麼多名人的包圍下,它作為作者唯一流傳後世的作品,卻是寫作於19歲少女之手這個事實,直到現在還是被廣為流傳的佳話。 關於它的副標題,也是值得津津樂道的話題。“現代的Prometheus”,這同作者丈夫的詩歌《Prometeus Unbounded》有什麼關聯?是否後發表的那個有受到先者的提示?不過這一些答案並不重要了,因為作者19歲時的初版中,小說里的敘說者固然是那個 Prometheus般的破禁忌者,而小說實際上的主人公卻是三個人,而且小說主題也同Prometheus的神話或寓意沒什麼聯繫。也許這只是一個隨手寫下的副標題,更有甚者,也許這是作者蓄意向讀者隱瞞她寫作的真實目的所使用的不同手法當中的一個。 這“諸多手法”,假設它們存在的話,其中一個必然便是作者丈夫所替寫的序言了。序言中說道:“我對於人性道德的關注,主要限制於對家庭內部親情以及人類德行精華的展示上。”這序言的作者,英國著名詩人雪萊,他的妻子便是那平生只有一部《Frankenstein》流傳的瑪麗·雪萊。
對這樣一部富於詩意的作品的主題,至今人們尚爭論不休。我並無意加入其行列,很簡單的理由是不管作者真正的主題是什麼,我只相信自己所讀到的,並且深信要多走一步必不可能,因而就有什麼且欣賞什麼吧。簡單歸納一下,我從這部作品中讀到的東西包括:無所不在的詩歌性,烏托邦式完美世界,人性本善的基本思想,作者對人性和知識啟蒙的設想(也是很具詩歌性的眩目),野心(某種男性特質)的摧毀力量,與此對照的以女性為象徵的親情。大致如此。 在那個時代女人是不去學校念書的,家庭教育(假如可能的話)便是她們教育的終點。在這情形下,有一個雙親皆屬知識界高層的家庭,與她作品的成功有着某種必然聯繫。她顯然博覽群書,書中給Victor以及creature所列舉的繁多書目便可證明這一點。她的知識並且不限於書本。《Frankenstein》一書對當時時興的科學哲學以及北極探險的密切跟蹤,體現了她知識的全面性。加上我上一段所列舉的諸多主題,這所有都在不到200頁的短短篇幅里展現,不得不說是對作者技藝成熟的確切證明。她並且還一定是個美貌的女人,至少年輕的時候是。雪萊為了她拋妻棄子,甚至引出其前妻自殺的悲劇。這等風流佳話,若不是年代實在久遠詳情無可得知,我一定會很有興趣去弄個清楚明白。但她的身世不可說不悲劇,少女時便託身相向的志趣相投的愛人,在兩人成婚僅六年之後便不幸身亡,不僅如此,因雪萊前妻之子擁有雪萊遺產的繼承權,瑪麗同她幼子的經濟都發生問題。為緩解壓力,她不得不籌劃重版〈Frankenstein〉一書,又在出版商的堅持下,不得不親自操刀,大幅修刪,由此便有了現在流傳最廣的此書籍1832版。
讀過或沒讀過此書的人或許會好奇,我在這麼個長串的標題和冗長序言之後,究竟要說的是什麼。事實是我已經迷失在自己漫長的思考之中。我是一個只能跳躍着前進的人,而在前前後後的跳躍當中,被自己思索構成的繩索的網所絆是太容易發生的事。如果我在寫的是某種“閱讀提示”的話,那麼我所能提供的僅只是:假如你用看待當時新興的工人階級和未被完全“解放”的婦女階層的眼光去看待那個不成功的實驗產物:the creature,這對你的閱讀多半不會有什麼害處。 讓我們再回到作者的身世,她的母親,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誕生後第12天,死於難產。她父母皆為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她的母親,以〈婦女權利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而著名。瑪麗仿佛要必然成為一個女權運動者。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有趣之處是,Frankenstein書中的女性角色全然是男性角色的附庸,仿佛只為給男子們提供親情之所而存在:Walton的姐姐是Walton寫信訴說心事的人,而她在書中未進片言;麗莎從頭至尾只是作為 Victor的“favorite animal”而存在,哪怕她實際上具有超出Victor的對真和美的信念和對世人的同情心;Justine,作為一個對完全無害的存在,背負冤名而早離人世;V ictor的母親,他們一家歡樂的源泉,也是以早早死去而結束在書中的出場;Safia,美貌的異族女子,只有她被允許稍許具有了靈氣,而這正是因為 the creature的慧眼之下,世人正是他們本來應該的樣子(?),而非Walton或Victor一類“唯我論”(同利己主義者不同,唯我論指的是一種以自己知識作為衡量一切標準的生存原則)者所能欣賞到的女性。 假如我們要堅持說作者在此書中表達的,正是一種婉轉的女權主義精神的話,那麼把the creature(一般被稱為monster的傢伙)作為一種與Walton和victor對抗的正面力量來看待,幾乎是必然的。
當我一個又一個地敲下“力量”,我心中不無欣喜地想到自己總算是離那個遙遠的目的地靠近了些。龐然大物的the creature的哀號聲會是什麼樣呢?當他在書的結尾翩然隱去在一片黑暗中後,抱着他在世上唯一的依託者Victor也死去的悲痛,雖然Victor的死,作為他一連串謀殺和陷害的終結不過是被他一手安排下的。他的力量是這樣一步步地將他引向絕路啊。 但我究竟說不清楚,力量,究竟是什麼?我印象深刻的記得多年前讀過某法國翻譯作品中的話,“你一度是我反抗世界的出色支持者。”正如有人將微笑一直掛在臉上,作為自己反抗世界的最後方式,不能避免地感到“反抗”的需要的我,一直苦苦思索關於“力量”的問題試圖以此找到自己的答案。正如為了相信真理,我們有必要相信Keats的斷言“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並放任自己去到對美的尋求中找尋至高的真。正如為相信真理而活,同為相信上帝而抵禦死亡的陰冷並無兩樣。正如信仰本身,正如Pascal 所說,“信了,是雙贏,不信,是皆輸。因此,何不信而贏之?”而精神巨人如歌德,也不免寫下這樣的話,“有誰不曾在夜半醒來/抱緊雙臂泫然而泣?”當所有人都不能自已地迷失在半途,有的人寫下一些警人之句用作指引他人的路標,我一路追趕地尋着這些路標而前,有時被引向錯誤的途上...路途的遙遠,使得終點反而盡在遠去了。我是否同the creature一樣,正在“力量”,那龐然不可控制的擁有物的指引下,走向自己的絕路? 然後我想到,如果是瑪麗·雪萊在想關於“力量”——她所創造的生物與生俱來以供濫用之物——的問題,她的答案會是什麼?
寂靜的夜晚,除偶爾的人聲之外,只有下水道傳來汩汩的水流聲。這是前幾天積下二十英寸的雪在迅速化成水去。陽光下,一切都無可遁形。 中國人相信萬物有靈,面對自然的純美而吸取其中的精華,用來作為自己的力量。基督徒的力量來自上帝的萬能,用夜夜的祈禱,換取安心的生存。那是否女性的力量便是來自反抗世界?——至少我在不斷地聽見她們這樣告訴我——或者說是,反抗作為世界代表的男性意志。我相信有一種力量,可以來自單純的反抗,一種持續地不間斷的堅決,一種意志對意志的較量。不過,也許還可以有別的.. 瑪麗·雪萊賦予the creature超人的體格,作為一個失敗實驗的產品,the creature具有了兩極分化的品質:極端的醜陋,和完美的力量。後者難道不正符合了victor心目中‘完美人類”,天生具有抵抗自然界惡劣境況的體質。不算太無稽的設想一下,假如the creature剛好面目優雅,豈不成了亞當的化身,他行走在人類之中,就象Wilde筆下巨人在孩童中一樣。假如說這一假設的不能發生,是因為瑪麗寫作的目的是她、她丈夫還有拜倫之間的“鬼故事競賽”的話,那麼在她給這個醜陋巨人接下來所安排的命運當中,則是另見匠心了。 the creature一入人世就被他不負責任的創造者Victor拋棄。他對自己命運悲慘的意識,是一點一點演化而出的。冷,餓,卻沒有給他預備下的衣服和糧食。並且victor是一見他就慘叫一聲,惶然走開了。他只好自己找尋食物,並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個素食者——某種意義上德行和自律的化身——並終身不變。他走進村落,村人們如Victor一樣的,慘叫着惶然奔去。他為此反倒深受驚嚇,得出結論不可讓自己被“人”看見。他摸到一戶農家後院廢棄的倉庫,發現在這裡休息比在樹下強一百倍,他對棲身之所感到滿意,就象身在天堂一樣。讀者可見,這個creature的溫良馴和,簡直如同野生的小動物一樣,或者乾脆是上帝派遣到人間的聖徒。瑪麗給了他哥特式的外表,和一顆純真如嬰兒的心。
在農家倉庫中的日子裡,the creature進一步認識了自己。這時的他不僅對自己的外貌有了認識——水中倒影——並且開始走進自己的情感世界了。瑪麗正在他身上做另一個實驗,“認識你自己”這希臘古訓揭示出,人之為人正是來自以自身為參照物對自己以及自己所身處世界的認識。由此,the creature越來越“象”一個人了,當他開始了以人類為標誌的思索。。 農家居住着的人們,是一幅微型社會圖,the creature透過牆上的小洞,日復一日地窺視着那一家人的生活。那些人們是多麼優雅啊。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流露着“人’的尊貴,而這正是 the creature所一心嚮往的。他幻想着有一天,可以走到人群中,成為其中的一員。他所要求的,不過是最基本的一點尊嚴和權利。幻想中的他還不知道,就是這麼一點點,就是他一輩子也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他憑着靈敏的心智(這點上他不比任何一個正常的人差)學會一點日常說話,通過對那家人的模仿——瑪麗至少在將他描寫成一個人,因為他的心智,還因為他同任何別人一樣,具有這模仿的本能——又在一個機會下,他學會了閱讀。他於是開始另一番自我教育,用偶然得到的書本,從中學到關於人類的知識:歷史,社會,人類起源(上帝造亞當)。他迫切地追索知識和語言,指望憑着通行證,去走進屬於”人‘的社會,獲得自己應當的那份溫柔之情。 他的渴望不可以說不正當:既然具有了做人所需要的技藝,他就應該被納入其中,他從裡到外實在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人,除了一點:他的外形。知識是他幻想中的通行證,可他缺少了實際上所有人都無形認同的更重要的一點,他看上去不是一個“人”。社會既然是這樣一個所在,身在其中者有一些公開宣任的準則,更有一些無形的準則。尤其是無形者,是因時代久遠而被人們所漸漸全盤接受,那是一些“不可為外人道”的社會存在之基礎,違者身受被社會排斥的命運,卻經常不知緣由。 the creature就是如此,他可以通過努力地看書來獲取知識,他天性馴和與世無爭。但他不能想到,不管他的思想和舉止多麼符合“人”的規範,只要他長得不象“人”,他就永遠不可能得到做“人”的權利。他其實一來到這世界就被永遠地打上了“另類”的標記,帶着這個標記,他早已被剝奪進入人世的可能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被剝奪做人權利本身,賦予the creature後來終生所靠也為之所害的力量。那些力量未經擁有者本人意識到,便等同於無。幸或不幸的是,the creature終歸會走到認識自己力量這一天。用古龍的話來說,“那是一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日子。因為就在那一天,我殺了一個人。” the creature的覺醒來自他不斷地被排斥。他滿懷好意地走向人群,卻被人群惡意相向,棍棒驅趕。他的覺醒來自他的憤怒。他的憤怒來自他的不解。他看着共同享受自然界的人們,不能理解為何自己一心向善,卻始終不能被接受,他救起溺水的小女孩,卻被及時趕到的女孩父親大打出手。他的憤怒只能用“以牙還牙”來解決——假如這算是一種解決的話——他最恨的,莫過於那個給了他生命卻沒給他任何其他生命的附帶條件的人。 我相信任何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着相似的憤怒。在悲哀於自身的命運之後,有要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他人並朝之發泄的欲望。the creature的情感之充沛,再次證明他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人”。為了不能得到的做人的權利,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大加利用。事已至此,作者對the creature的描述依舊蘊涵慈悲之心。他並非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殘暴的殺人狂。剛好相反,他甚至還在指望同人類達成某種程度的友好關係。他路遇獨自玩耍的victor的小弟弟,突然想到兒童不同於成人,也許會對他這麼“異類”多少不那麼排斥,於是同小孩說話,想讓孩子陪他過日子。他馬上發現自己又異想天開了。這小孩對他流露出的由衷的恐懼和憎惡一點也不比成人少,更有甚者,他發現這孩子竟然就是他念茲在茲的仇人的親弟弟。於是在一種瘋狂情緒的支使下,他扼死了對方。這是他的第一次殺人,照美國刑法來說,是在“被告人不能支配自己情緒和意志”的情況下發生,算得上無辜的。倒是他把孩子胸口小像取下來放進路過女子Justine的口袋裡陷害對方之舉,照他說法是用“從人世間學來的惡作劇”,透着真正的惡意,而這最初的“惡”,不過是他“學來的”——作者在描述the creature的“善”的同時,給了他一個多麼反諷的參照物啊。那充滿“惡”的人世中人,卻是個個盡把the creature當作是‘惡“的化身來着,僅只因為他的外形,就給他打着終生不改的被放逐的標記。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5: | 想起了抗日英雄任常倫 | |
| 2005: | 諧和: 美加邊境遭遇 | |
| 2004: | 清明節的懷念---2004 | |
| 2004: | "受賞"日本電影 "鰻魚& | |
| 2002: | 剃鬚 | |
| 2002: | 一棵開花的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