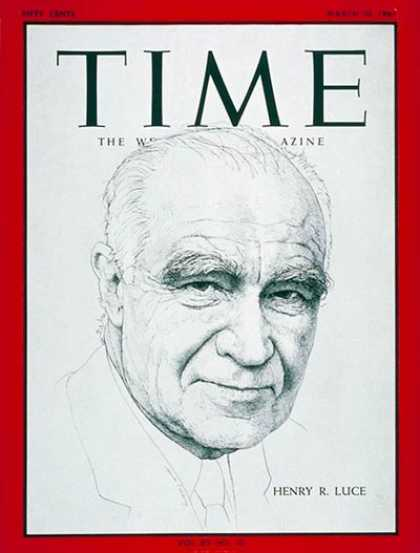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Henry R. Luce)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
20世紀初的二十幾年裡,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國“ 還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個地域廣大,貧窮落後,無關緊要的陌生國度罷了”。即便還有些廣聞博識的美國人,在他們掌握的由來已久的中國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畫式的怪誕想象,如“男人留着辮子”,“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時撓腳不撓頭”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險的形象,從之前流行的“黃禍”恐慌到尚在執行的《排華法案》,都說明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何等惡劣。
然而,即便是這種情況下,也不乏對中國充滿好感的另類。在耶魯大學的校園裡,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國的美國學生,他在一首詩中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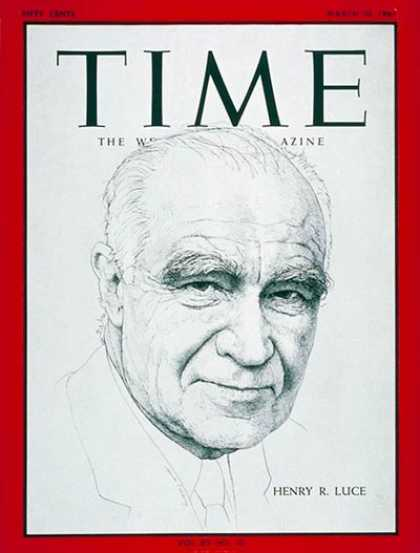
“啊!給我一乘山東軒子,讓我來嘗試一下騾夫的生活。
啊!給我一副擔子,走向那綿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尋當年的開拓者。
告別了,上海江邊停泊的輪船,還有那古老的篷帆。
當風雹驟緊十月之後,我們將重新見面。……”
年輕人對中國的偏愛在此表露無遺,以至於詩中竟有些鄉愁的味道。而十幾年後,他更是憑藉着一個強大的出版帝國,把這種好感散播到了整個美國。這個美國學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時代》創始人——亨利.盧斯。
盧斯的中國
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此時,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國會議員,下到美國公眾對於這場戰爭依舊奉行着“孤立主義”的態度。赫斯特報系的一條新聞標題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國公眾輿論當時的情緒:“我們表示同情,但這不是我們所關注的事情。”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則說:“國會對這場大戰的根源進行的調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約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戰的公民所掀起的運動等等,都顯示出美國人多麼不願主動地捲入世界事務。”(《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然而對於這種氛圍,亨利.盧斯卻大為不滿。盧溝橋事變後,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依舊停留在口頭譴責的層面上,甚至,“暗地裡”仍然“履行合同”,繼續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貸款,為此,盧斯曾不斷公開批評美國政府,甚至在《時代》上撰寫社論,認為美國應當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停止對日本的資金援助,轉而將援助“贈送”給中國人。
不僅如此,當時因戰亂有大量中國學生申請赴美學習,盧斯還積極為留學生購買寓所,並成立美中協會,作為中國政府在美事務的代理機構,盧斯親自兼任董事。此後,盧斯還為救濟中國聯合會的組建,積極出資出力,為支持這一組織倡議的對華捐款,他曾親筆寫信給全美《時代》周刊的訂戶,募集資金24萬美元,成為援華個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這也不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美國之外盧斯最愛的國家,當然,盧斯之所以對中國如此友好,與他的身世密切相關。亨利.盧斯的父親路思義,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當年,路思義從耶魯大學畢業時,放棄了回鄉做律師的打算,轉而決定將一生獻給傳教事業。1897年,與老一代在華傳教士一樣,路思義胸懷着福音傳遍全球和拯救億兆東方人靈魂的雄偉目標,來到山東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個兒子盧斯,便誕生在了這塊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此後,路思義長期地在中國生活、傳教、辦學。這種生活也深深影響着漸漸長大的兒子,據說,盧斯五歲的時候,便可以向鄰居的小夥伴即興地發表自己的布道。14歲時,盧斯才返回美國,儘管此後,他並沒有繼承父親傳教布道的衣缽,但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盧斯卻成功地把宗教傳統和中國納入了他後來的出版事業中,在對世道人心的宗教關懷及對中國的喜好等方面,他與父親則是那麼的相似。正如他來後的部下、《時代》雜誌駐莫斯科記者約翰.赫西所說:“盧斯註定不會成為他父親那樣的靈魂拯救者,但他成為了他父親那樣的籌款能手,而且目標都是中國。”童年的中國經歷對於盧斯的影響實在太大,與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說:“只要跟盧斯長久相處,就無法不感到他對中國親人一般的關心。”
因此,在美國的“孤立主義”的氛圍依然濃重的時候,亨利.盧斯就率先以時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體為陣地,開始了對中國戰爭局勢的連篇累牘地報道。
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時候,儘管盧斯有着影響非凡的輿論工具,某些援華的慈善機構也加倍努力地工作運轉,但並不足以打造出一個讓全美國公眾感受強烈的理想的中國印象。盧斯意識到,要吸引美國人注意中國,必須向美國人出售一個全新的正面的中國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戰爭爆發後,盧斯為中國不斷地搖旗吶喊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儘管國民政府展開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動,以求得美國等主要國家的援助,並爭取這些國家對日本施加壓力,甚至實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並不明顯。對此,盧斯認為,由於長期以來積弱的國力,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於從屬與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國在美國人民中的形象並不十分樂觀,而“形象”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
這樣,如何在美國公眾輿論中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就成了能否爭取到美國援華抗日的關鍵。盧斯認為,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國人的注意,必須要從中國那裡尋找到美國人熟悉的理想和價值。於是,他開始精心設計出一種所謂“中美相似”的觀念。
比如,中國與美國在地理、歷史上的簡單類比,是盧斯的雜誌在較長時期內比較熱衷的一種表達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時代》雜誌中就曾有文章這樣介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國的波士頓(北京)、紐約(上海)、和華盛頓(南京)後,正在向中國的芝加哥(武漢)進發。”與此相仿,廣東又常常被比照為潮濕、悶熱的新奧爾良,外蒙古則被認為相當於美國在阿拉斯加的領土。又如,1941年4月的《財富》雜誌中說:“當你看到國民黨,你會想到民主黨,當你看到重慶的工廠企業,你會想到匹茲堡。”這樣牽強的聯繫雖不免有些滑稽,但盧斯最終卻使得即使是農夫或家庭主婦也能設身處地地關心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政府的種種舉措也與盧斯的輿論攻勢“不謀而合”。深曉對美宣傳利害的蔣介石,多番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國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並密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積極聯絡在華美國記者,以擴大對美宣傳,抵制日本對英、美輿論的收買。
另外,自30年代以來,蔣介石不僅與當時美國最大的媒體帝國老闆——盧斯保持着良好的“私誼”,而且,為了顯示出對美國的親媚,蔣的國民黨政府也處處表現着強烈的美國色彩。在中國採訪多年的《時代》記者白修德說:“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像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那樣徹底地被‘ 美化分子’所滲透。……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說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這個政府中,上至總統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員隨處可見美國名校的畢業生,白修德打趣說:“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而在美國,經過盧斯對中國堅持不懈地正面報道,一個抵禦外侮、蒙受苦難而堅強不屈的“時代中國”形象,也漸漸浮出水面。
“時代中國”
在當日的新聞報道中,中國儼然是反法西斯戰爭中“崛起的英雄”,到處是士氣高漲、英勇抗敵的官兵及守衛故土、抵禦外辱的勇敢的人民,盧斯說:“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民這樣,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擁抱着和平、寬容和正義的理想。”
不僅如此,他們還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一個肩負着復興中國大任的基督教國王——蔣介石”。作為一國的首腦,蔣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期間,時代公司的主要媒體對蔣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國人的各種價值期望。
蔣介石的發跡史被報道成一個很適合美國公眾口味兒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時代》記者的筆下,蔣介石是一位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的統治者,他與孫中山結識後,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孫中山,為中國實現民主進行着不懈的努力。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面對壓力從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圖分裂中國的將軍、元帥、同僚及自由的冒險者”進行着鬥爭,最終“使他成為一個一流的鬥士,並使他手下的人都對他心悅誠服”,這樣的個人奮鬥史顯然更能引起美國公眾的興趣。
蔣介石“虔誠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盧斯大書特書的內容。比如,《生活》雜誌對蔣介石1931年受洗禮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並分析認為,“像蔣介石這樣有着堅強意志的人是不會輕易皈依一個信條的”,蔣介石接受一個宗教也不是為了出名,那麼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年《時代》對西安事變的報道,則展現了蔣介石聖徒一般的感人行跡:文中說到抽大煙的邪惡之徒張學良與匪首楊虎城綁架了為這個民族帶來民主與基督精神的國家領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艱苦日子裡,蔣介石仍然每日誦讀《聖經》激勵自己,“他感覺自己就像耶穌在曠野中的那四十個日夜,將按照上帝的旨意領導中國走出苦難”。在時代公司的報道中,蔣每日的生活細節也都充滿着濃厚的宗教氣息。例如,蔣會在每天早上的5點30分準時起床讀聖經,他平日總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結合在一起,來作引導他的軍隊。另外,蔣在一些傳教士的幫助下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也是頗能感染美國公眾的重大事件,美國人甚至將其視作一場體現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運動。
盧斯的影響
當中國正值抗日期間,也是盧斯的事業獲得空前成功的時候,其影響力和財富也達到了巔峰。“《時代》已有15年的歷史,仍然沒有任何的競爭對手,是唯一全國性的新聞來源。”盧斯控制的《生活》雜誌雖然剛創刊不久,但“已經在美國新聞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圖片和注重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為美國當時“最令人興奮”的雜誌。
正如人們所評論的那樣:“說他們是輿論的喉舌也很確切”,“既影響了人們思考寫什麼,也能影響人們怎樣思考”,盧斯所創造的中國神話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美國,“廣泛地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同情與敬慕”。
據1937年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最關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戰爭僅次於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災,位於第二位。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同情也從 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畫報的讀者在看過雜誌上反映重慶遭日軍轟炸的照片後,難以抑制心中的情緒,來信說:“我非常讚賞你們所採取的對中日雙方同時進行報道的政策,因為這幫助美國大眾了解真相,並進而支持我國政府採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戰爭原材料的政策。”當然,盧斯的影響遠不止僅僅是在普通民眾之中,曾短暫訪問華盛頓的丘吉爾在感受到當時美國上下的氛圍後,曾說:“我已經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層人物的心目中,具有異乎尋常的重大意義。我意識到有一種評價標準,把中國幾乎當作一個可以同英帝國不相上下的戰鬥力量,把中國軍隊看作是一種可以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的因素。”丘吉爾對羅斯福表示,美國輿論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估價太高了。總統卻“大不以為然”,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有五億人民,如果這樣眾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紀裡那樣蓬勃發展起來,並且取得現代化武器,那時會怎樣呢.
盧斯的努力讓美國徹底把“孤立主義”拋在了腦後,公眾輿論的高漲,使得美國政府在採取對華援助的時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況下,美國先是對日本石油禁運,進而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宣布對日作戰。同時,在不斷的新聞輿論壓力下,也逐漸加大對華物質和軍事援助。在美國工商界,盧斯的宣傳也收到了積極的效果,隨着商界巨頭小洛克菲勒、摩根財團的摩根、國際通用機器公司總裁沃森等一個個成為親蔣分子,美國商人隨之而來的對華投資和貿易也迅速擴大,中美在40年代的經濟聯繫不斷加深。
美國世紀
然而與此同時,盧斯在塑造中國形象的時候摻入了太多理想主義的成分,比如越到後來,他一廂情願地欲以美國方式改造中國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顯。盧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實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擴張願望急劇增強的時期,國勢的強盛使得盧斯在美國制度和文化優越性上堅信不疑,因而面對一個貧窮、落後而又戰亂頻仍的中國時,盧斯深信一個強有力的基督教戰士領導中國走美國式的道路是中國由弱變強的不二法門。因此他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青睞有加,更寄望蔣的國民黨政府能按照美國模式來改造中國。
美國總統柯立芝曾說:“美國人是理想主義者,美國是由理想主義組成的民族”,盧斯晚年回憶時說,童年期間,他由山東回國探親,親自感受到美國的富裕之後,就開始“形成了關於美國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觀點”。長大之後,他理想化的美國觀則更加狂熱,在大學畢業的演說詞中,盧斯就要求美國擔負起世界領袖和國際警察的責任。而1941年,他所發表的《美國世紀》一文更是將其觀念公諸於世。他說:“(美國應當)全心全意地擔負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生命力國家的責任,……為了我們認為合適的目標,通過我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對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面影響。”
他說,如今美國已成為世界的知識、科學和藝術之都,除此之外,美國“還繼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來所有偉大的原則”,如主持正義、熱愛真理、樂善好施等;而這個時代,美國應當“將這些理想傳遍全球,投身於使人類擺脫貧困”的“近乎天使的神聖工作”。
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人不應該“獨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濟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國家發展;正因此,盧斯認為美國政治、道德和經濟的強大力量會幫助正在尋求救亡圖存道路的中國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堅信總有一天中國會按照美國的模式發展。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作祟,盧斯對中國的報道漸漸脫離了它實際的土地,當年《新民晚報》曾這樣評論:“盧斯既沒有與普通百姓交往,亦與大眾日常生活無關,如果他憑藉他的觀察討論中國問題,則僅僅有助於為中美關係增加一些誤解。”
失去中國
1942到1943年間,宋美齡訪美,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在此達到了高潮。宋美齡在國會的講演,贏得了空前的掌聲,講演又通過廣播與雜誌報紙傳遍全國,贏得了美國大眾的歡迎。她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地的講演,每場聽眾都多達數萬人。《生活》曾這樣描述當日的情形:“他們從未聽過如此精彩的講話”,參議院們被她地道的英語和寧靜持重的神情驚呆了,“夫人個人和思想的潛在魅力早已註定了她此行的巨大成功”。受到宋美齡訪美空前效應的影響,1943年12月,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困擾中美關係60年的《排華法案》也被廢除。
然而,就在宋美齡在美國享受空前榮耀的同時,《時代》駐中國的記者白修德卻發回了觸目驚心的關於河南災荒的報道。此後,關於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政治專制、軍事無能的消息經在華軍政人士的報告和新聞記者的報道後,日益引起了美國國內的目光。
漸漸看清真相的《時代》駐華記者白修德,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報道原則,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全然批判的口吻,這樣他與盧斯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儘管二人有過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儘管盧斯曾對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實情況備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想法與盧斯所遵循的美國政策越來越遠。因為,在盧斯看來,只有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才能建設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發揚基督教的精神,這樣才符合“美國世紀”的理想。
盧斯繼續“保護”着蔣介石,而白修德曾想方設法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真實的報道發回美國,但這些報道又免不了被盧斯派人修改,許多報道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後出來的也是“一個充斥謊言、完全虛假的報道”。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周刊準備以蔣介石作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傳,白修德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
到1944年11月,白修德稿子已經在《時代》周刊發不出來,但盧斯所塑造“時代中國”形象卻依然發揮著作用,這反映在對華政策上則表現為,抗戰勝利後美國終於採取了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傑斯普森在《美國的中國形象:1931-1949》一書中指出:盧斯等人通過媒體誤導虛構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失誤以及最後“丟失中國”的結局。也許,它的影響還要深遠。新中國成立後,盧斯依舊扶蔣###的宣傳,在共產主義的威脅增強的情況下,公眾的緊張情緒上升,因而又使得國內一大批有才華的亞洲問題專家及外交官受到迫害、打擊,亞洲問題無人敢問津。正如斯萬伯格所說:“如果沒有盧斯,沒有盧斯新聞帝國,就沒有院外援華集團,沒有麥卡錫議員,沒有‘失掉中國’造成的全國性歇斯底里,也沒有越演越烈的必須停止亞洲共產主義在美國泛濫的恐懼……”
晚年時,盧斯曾問手下的一位編輯“多大了.”對方回答:“29歲。”“我多想回到你的那個年紀啊”,盧斯感慨萬端:“我是在中國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個地方已經被共產黨接管了,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到它變成自由之鄉。”
在美國,沒人懷疑盧斯是少數真正關心中國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國始終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這也許是其一生中最不該的想法。(《誤讀中國1000年》 作者: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社劉永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