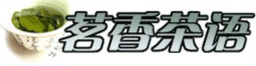| 上海,七年之癢 |
| 送交者: 西山夜話 2023年08月20日16:30:46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
上海,對於我來說,即無無牽掛又無根 ,呆久了就想逃離。況且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外面有太多的誘惑呢?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綠皮列車在夜幕里將我由北站送進上海,從而有幸開啟了人生一個新時期,七年後又將我由北站送出上海,匆匆告別了那個七年人生。當時並未意識到,竟是一去不復返。可以想像如今那裡肯定是物是人非,然而過去了的一切,都是我美好的回憶: 南京路的人流,淮海路的梧桐,徐家匯的教堂,華亭路的攤頭。五角場的陽春麵,豫園的小籠包。蘇州河水即使再熏鼻也未曾阻止駐留在橋上片刻的衝動,外灘一眼望不到邊趴在防浪牆偎倚私語的情侶再擁擠也未曾擋住去那裡以別人浪漫填補自己荒蕪心裡的念頭。 襟海帶江,人潮如涌,那是一段少有的即無運動也無折騰,休生養息,萬物復甦的辰光… 在我的腦海中,乘載着我的時代列車已經遠去消失,,然而,那個年代與我擦肩而過萍水相逢的普普通通的上海人。沒有消失,哪些與我朝夕相處的人們卻愈加清晰。
我最初對上海人的印象或是來自小說電影或是人們的口口相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的母親從縣城醫院下放到農村公社第一件事就是護送一精神受刺激的上海女青年回滬,行前小住我家,母親到滬並在其家陪護數日,回來說這位女青年的母親一生中竟沒有走出過閘北區,這件事對我以前腦中的上海人經多見廣的以偏代全的誤解觸動較大。 我本人最先與上海人的接觸可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插隊務農時期,當時與他們一塊插秧,一起割麥,一排除草摘棉,一塊集聚生產大隊或公社參加政治學習和大會。甚至打打鬧鬧。我的接觸中,大多數人是正面、積極的,有的人皮膚曬得黝黑正亮,其吃苦耐勞不亞於生產隊的壯勞力。他們的陽光和樂於助人也使人耳目一新。與他們相處也是非常愉快的。 在上海的七年中,儘管大部分時間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但從有限的時空中也不免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們,從而加深了對上海人的了解。 與上海同學同居一寢室,同聚一教室,更是朝夕相處。他們中間有我的良師益友,他們對我的幫助至今未忘。 雖然我敬重的老師長輩都已離世,但仿佛他們又沒有走遠,當年的同學和朋友現在雖”相忘江湖“,有時會有一種相濡以沫的感覺… 在上海的最後的三年,得益於上海淮海路舊貨商店買到的除了玲不響渾身都響的自行車使我經常走街串巷成為可能。周末大都去徐家匯交大遠房表舅家渡過,跟他一起買小菜,看着他做飯與鄰里互動。聽他們聊家長里短、油鹽醬醋材,感受着里弄人們的喜怒哀樂。 在上海的最後一段時間裡,陰差陽錯,有機會深入江南造船廠和寶鋼,與青年工人們座談交流。記得當時被組織者分派的是《世界經濟發展趨勢與我們的對策》的話題。儘管當時憑藉信息不對稱的優勢,有忽悠之嫌,但與青年工人們交流坦陳,同時也從對話中了解到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收益良多。 七年的上海學習和生活,短暫而有意義。七十年代末從上海北站進,八十年代中又從北站出,仿佛是一瞬間,記得在上海四年結束時聽上海話還懵懵懂懂,到了第七年已基本明白說的是啥了。我也意識到是該離開的時候了。 而印象最深的是我所接觸到的絕大多數的上海人,陽光、積極和正面… 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工商科技在整個國家經濟中舉足輕重,註定了上海人群無法逃避地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而每次時代大潮呼嘯而來和頹勢而去,官、商、學的一些人眼看着他們或飛黃騰達,或沒頂之災,但大部分底層人們仍叫天不應,不得不承受着受的時代的蹂躪和玩笑 。開埠一百八十年來,上海,上海人遭受的時代強加的蹂躪和玩笑從未間歇過。況且,當整個民族都如坐過山車時,上海人怎可能獨善其身呢? 上海人,其本身就是源於各地人之匯總,除了方言口音習俗有別外,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有的陋習和發光點,上海人同樣應有盡有。 然而,相較於其他地域的人群,上海人,不管是祖輩久居那裡,還是出生在滬;不管是父輩移民,還是自己在那裡生活多年。做為一個集合名詞或是血有肉的群體,長期以來飽受着某些誤讀: 什麼男人怎樣,女人如何,文化藝術及學術界更是“衍生出”什麼“海派,諸如此類臉譜化的不實劃分和定義。 也許是常常將由影視小說或道聽途說信以為真,並不知不覺地養成以點代面,以偏概全,以至於自己對一件事、一個人評價,失之偏頗原因吧。 其實,不論是鳳毛麟角,還是支撐桌子腿的瓷碗碎片,大多數上海人,不僅亦師亦友, 而且宜師宜友! 回顧過往人生,是時代的浪潮將我裹挾到黃土崗,又將我從那個犄角旮旯的地方衝進繁華上海,爾後推到北京經濟權力中心的邊緣。浪潮再次發力將我卷到世界銀行總部,回流後,二次登陸美利堅西岸,最後在西北一隅裹足不前,平度餘生。 而我在上海渡過的七年,尤為難忘。因為在那裡,從教授我《西方貨幣銀行學》系主任講述他在喝哈佛喝墨水時老師家中特設一間空屋做為思考的故事,認識到在人生中思考是如此的重要。從因言獲“右”教授經歷的坎坷而處變不驚,砥礪前行的精神,矯正了我以後人生前行的態度。從導師的誨人不倦,給予我極大的自由,感受到老師的寬容和和藹。從因幾位同學坐在草地上質疑正統激進理論而被市委《思想動態》點名通報事件,系、所教授們聯合起來,頂住層層壓力保護我們的插曲,體會到什麼是應有的“師道”。 上海七年的生活後,雖然上海話勉強聽懂但不能張口,當回憶那段時光時,對於上海及那裡的人們,不管是擦肩而過還是朝夕相處,我還是想用當年回敬有助我的人們那樣,說一聲: “老師傅, 暇暇儂!”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22: | 古今中外愛國者如是說 | |
| 2022: | 零下三十度,Alone and Cold | |
| 2021: | 我的阿富汗同事 | |
| 2021: | 佛陀並不打算剃光每個追隨者的腦袋 | |
| 2020: | 替班農辯護(ZT) | |
| 2020: | 貼張圖,我的非工作電腦桌面的backgrou | |
| 2019: | 一個英雄和三千懦夫 | |
| 2019: | 90年代自費留學生交培養費的問題,用MA | |
| 2018: | 飛星哥哥呢,我後面回你帖了。 | |
| 2018: | 斜拉橋和懸索橋之比較,圖片來源於網絡 | |